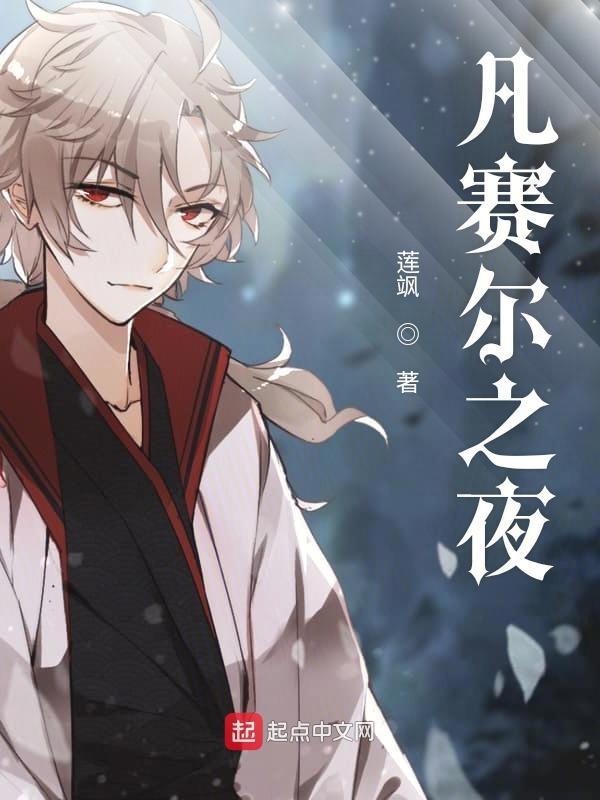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此地空余黄鹤楼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医人对辛时的请求始料未及,愣一愣,下意识往外看,问:“辛待诏有何吩咐。”
膝盖痛地很厉害,辛时下不来榻,只能勉强支撑起半身行礼,道:“臣谢皇后恩典。医者仁心,我们也算半个同僚,不管看在哪一点上,可否请你……用药痛快些,以及,走时帮忙劝一劝宋嗣王,别让他太早知道。”
医人诧异道:“辛待诏在胡言什麽?”
辛时糊涂了。医人的表情不似作僞,他迷迷糊糊道:“你不是奉皇后之命,来……”
来杀我洩愤的吗?
“话不能乱说!”医人听出辛时话中意味,急忙喝止。“陛下与中宫关心待诏因公致病,故遣某来诊问,何以歪曲圣意?我们按敕办事,做什麽都是有依据有章程的,这番影射闹大了无人担待得起,慎言!慎言!”
除却两位圣人,辛时已经很久没被其他人训斥,头上受伤脑子又有些转不过来,听得一愣一愣。医人的脸色也有些僵硬,写完药方例行按照规矩叮嘱几句,不複来时热络,整理东西离开房间。
女使又来门口说了什麽,随后脚步渐远,连杨修元的声音也不知何时消失。家中彻底安静下来,不多时芝奴推门走入卧房,见辛时还愣愣地坐着发呆,道:“阿郎,他们把十二郎劝走了。”
辛时不说话,望芝奴一眼,回神后又开始头痛,忍不住深皱眉头。芝奴扶他躺下,注意到桌上留下的药方,拿起问辛时道:“上面的药要抓来吃吗?”
辛时有气无力道:“拿来我看看。”
他伸出一只手抓过药方,朦胧中看到上面用粗浓笔墨写了十几味药,芦根、牛蒡子、桔梗、甘草、黄芩……确实是最常见治疗风热的药,也没什麽用量问题,只不过一味更比一味苦。
辛时头晕脑胀,将药方胡乱望榻前一塞,道:“要吃,按医嘱吃。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伤风病人……”
杨修元走后,家中彻底安静下来。
奴拿着药方出门抓药,不巧离家最进的药铺没有干竹叶。芝奴回家报告,辛时休息半天又有些精神,闻言道:“缺竹叶不要紧,明天早点出门,到别地药肆里补上。买到的药今日先煎,不全不要紧,不能不吃。”
他可不敢再阳奉阴违,这趟鬼门关虽然算是走过,到底惹怒了神后。芝奴得了主人命令出去,同样摸不着头脑,将药包拆开一股脑倒进陶罐里,对阿衡道:“银花,连翘,薄荷,这都是疏散治热的药。宫内郎中给阿郎诊治风寒,他分明没发热,真令人糊涂。”
清苦的药气弥漫开来,终日不再见第三位访问者。天色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厨房又腾起淡淡的米香,辛时喝半碗粥黍米粥,开窗换气见落日夕照强烈,刺得人睁不开眼。
芝奴将药浆倒出来,黑漆漆满满的一大碗,放至半凉后送给辛时。辛时一口气闷下去,腥苦的回味沖得好容易平静的头痛再次作祟,晕乎乎道:“再给我盛点米浆。”
有捣药声“叮”、“叮”传来,阿衡捧着药钵进门,里面是深绿湿润的药泥。她替辛时解开身上的纱布,一层层卷开后是敷过一天后已经变黑的药渍,阿衡小心翼翼地拿竹签刮开,然后拿细纱布蘸过水,去擦伤口上残留的旧药。
伤口色泽暗红,边缘有些红肿,破皮的新肉惨白又粉嫩。痛倒是不怎麽痛了,辛时任由阿衡给她换药,问:“要涂几次?”
“肿消下去就可以不涂了。”阿衡欲言又止。“阿郎从马上跌下来,擦了髒物。天气热,伤口不宜多捂。”
辛时“嗯”了一声,见阿衡替他包起手臂又开始处理腿伤,一道道狰狞的红痕仿佛入骨,问:“能不能走。”
阿衡摇头,道:“最好不要。”顿一顿,又道:“阿郎颅骨有损,医人嘱咐卧床休息一旬。”
果然是砸伤了。辛时不再说话,主仆相对无言,直到阿衡揭开头上纱布,才又道:“拿镜子给我看看。”
乌金入地,晚霞也将烧尽,星河影影而现。铜镜倒影出的人像十分模糊,阿衡从桌边举来灯,依旧看不真切,辛时凝神片刻又觉心力不济,松手让圆镜落在被褥上,叹道:“算了。”
等阿衡包扎完毕,又道:“打点水擦脸。”
阿衡依令出去,和芝奴在院中遇见,言辛时情况尚可。两人身影交错,阿衡到旁院打上井水继续服侍辛时,芝奴领着灯各处查看。这只是例行检查,曾经的曾经是杨修元负责过的事情,芝奴半在意不在意地浏览过家中每个角落,正要把灯拿回自己房间,听门口簌簌的动静,似是有人在外徘徊。
芝奴心有疑惑,打了灯又过去。这一看不要紧,墙头上一个人影正在往下跳,落地时激起薄薄一片灰尘。灯光映照出他的面容,芝奴当即倒吸一口凉气,失声道:“外面宵禁,你打哪冒出来的?”
杨修元不答,往地上一撑,站起来不管不顾往里面跑。芝奴一把伸手去拉,没捞着立刻转身跟着他往内跑,边跑边大喊:“十二郎!站住!”
他好容易抓到衣角,立刻被甩开,跟在杨修元身后穿过堂屋却不幸被椅子绊住。芝奴扶住噼里啪啦乱倒的桌椅,一边稳住身形,一边又喊:“翻墙闯民宅,你……你犯法啊你!”
杨修元充耳不闻。他已经走下台阶,再有十几步就要走到辛时门前。芝奴这下真慌了,顾不得被撞歪的桌椅急沖沖再度追上去,道:“阿郎不见你。十二郎,十二郎,你别任性了,使不得——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