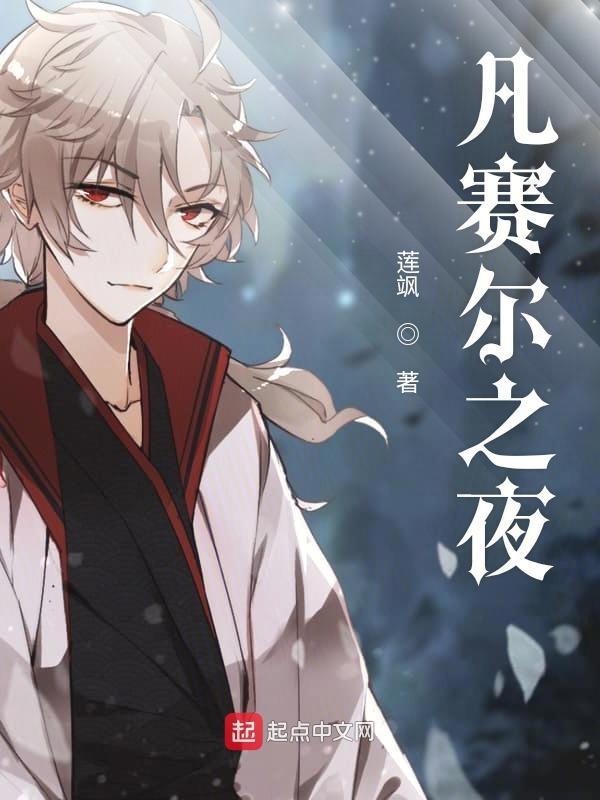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七院诡案录cp简介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进了正殿,殿里也没人。倒是殿内大门左边放着一张小木桌和椅子,我知道这是捐款登记,如果有香客捐款的话,就会把名字和金额记录在这本本子上。
现在椅子上没人坐,本子摊在那。我随手翻了翻,纸质已经很脆了,显然有些年头。上面的笔迹差别很大,或许是让香客们自己写的也说不定。大多数的金额都只有五块十块,一个月加起来大概不到一百。我不太清楚中国宗教建筑和里面工作人员的经费来源,但是只看这个的话,连水电煤都不可能支付起。
这时候,胖子在大殿的后门口叫了一声,让我过去看。后面是一排厢房,胖子说,你看那会不会是他们住的地方?兴许人家每周一上班呢?
那里的确很像道士们居住的房间。有六间屋子挨在一起,每间都不大。我和孟师兄俩一个从左一个从右,不管找到谁就先问起来。
我走了左边。这片地方同样安静,连鸟雀声都没有。从窗口望进去,几间房都是空的,看到第三间的时候才看到点生活气息——这间屋子里有住过人。从窗口能看到里面有基本的生活用具,还有几个小电器,一个台式电脑,书桌上堆满了东西。只是屋里也没有人。
我左右看了看,没人。再看那门锁,就是最老式的那种单锁,于是就狠狠心,拿出交通卡来把锁划开了,推门进去。
进屋之后,我一眼就看到了书桌上有个眼熟的东西——那个红绳挂的铜铃铛。拿起来掂了掂,发现比想象中要重很多。
电脑的主机箱有风扇声,它应该没有关机,只是待机。我动了一下鼠标,果然屏幕亮了。不过这人的电脑屏幕很干净,就是几个系统程序和一个文件夹,那是人家的隐私,也不能乱看——虽然翻外面也算是侵犯隐私了,但至少我心里会过得去些。
他的书桌真的够乱的,上面什么都有,从电路维修类的东西,到久病卧床病人的养护(这都什么玩意),还有几本古籍线装书,一大堆手写纸。其中的一张上面写了个地址,这地址挺眼熟的……我想了一会才想起来,这是七院的地址。
翻开上面最凌乱的一叠,我见下面有一本剪报本,看标题似乎都和医院有关系——翻了几页,那都是和七院有关的新闻。有一条甚至是从一张二十多年前的旧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应该是七院开始扩建病房区,也就是如今的旧楼),最新的就是上次张志仁的事情。
这个人在调查七院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隐约觉得奇怪,又翻了几页。紧接着,我在剪报本里发现了自己的照片。
哑巴昆鸣
这是什么情况?
我看着剪报本里自己的照片——以及一段很官方的简介,大致就说了学历,师从和专业,曾经参与过什么什么研究,发表过什么论文。这种简介随便哪个上进点的医生都会有,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做简报的价值。
在我的照片旁还有一行小字:12-3,8:35?
这应该是日期和时间,不知道有什么特殊意义,尤其是后面那个问号。
在我的照片简介前后的新闻都是六月初,也就是张志仁失踪前——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他为什么要做这份剪报?
我心里实在是一团乱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那本剪报本塞进了自己的背包里——就像是游戏里遇到一个纠结无比的任务,干脆就先跳过它,去做其他任务升级,然后再回来慢慢折腾。
他的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其中包括一本通讯录。这种本子在上一辈人手里很常见,昆麒麟的这本也是,皮质封面,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电话地址之类的联系方式,很旧的样子了。我前后翻了翻,这本里面倒是没有我,只是其中一页贴了记号的纸很引人注意。
其他纸上都是写满了密集的通讯方式的,只有这张纸,它上面只写了一个人的联系方式。最前面是电话号码,然后是一串地址,北京的。而这个联系方式则属于一个叫做蝙蝠余的人。
蝙蝠余?
我想起这个人了,就是那个余少爷,自己把自己眼睛给玩没的,来换了个什么天眼。整本通讯录只有这张纸上贴了张蓝色的标记贴,显然极其重要。我留了个心眼,用手机把它拍了下来。
其他的翻了一下,有道观的账本(果然出多入少),还有张学费清单——学费清单?学费?
单子上印的是一所叫做宁华中学的学校,我没听说过,估计可能是什么私立学校。有住宿费说明这是寄宿制的,费用是两千元。
学生的名字叫昆鸣,现在在读高一。看这个年纪肯定不会是昆麒麟他孩子了。
不过这个发现让我更心塞了——不管这两人什么关系,昆麒麟可能现在是供着一孩子过日子的,这人如果真出什么事,那孩子怎么办?
我没心情再翻下去了,把东西尽可能放回去,就准备离开这。但是就在我转身出去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门口站了一个人。
这是个少年,十六七岁样子。穿的是白色夏季短袖校服,还系着红领巾。庭院寂寂,这少年就安静地站在门口,秀气干净。
他只是看着我,不开口。我站在屋里,就觉得尴尬得要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人这样对看了半天,我干笑两声,“你……认识昆麒麟吗?”
他依然盯着不说话,过一会才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是附近的学生吗?放学了别乱走啊,爸爸妈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