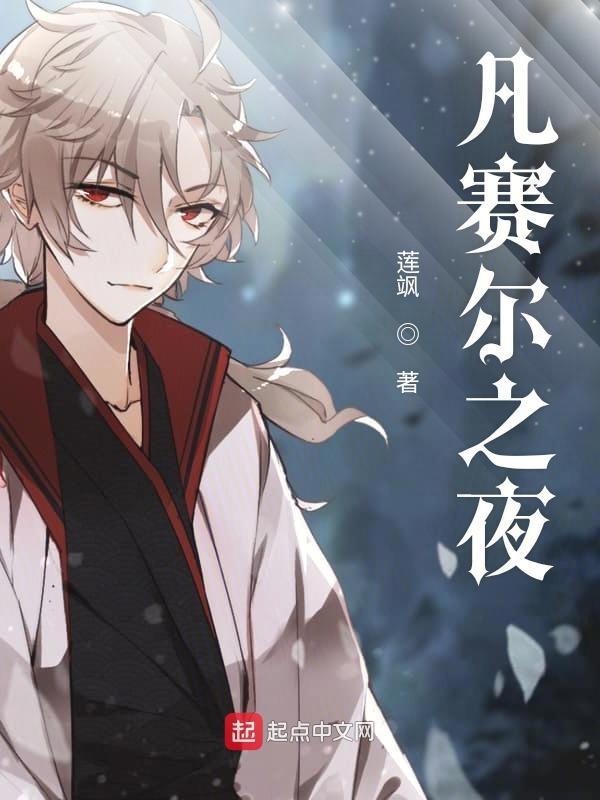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1v1) > 第69章(第1页)
第69章(第1页)
他告诫她莫要去惹事,她照旧每日都出府,既然他那些话她都不入耳,又哪里来的不高兴?
他淡淡收回视线,“不说也无妨。”
宋南枝看着他的背影默了几息,忽然答:“我去了宝斋。”
不仅去了,甚至他与太子谈话时,她也亲耳听见了,是他们把供词说出去的,利用她爹来做局演戏。
沈洲总说她心机利用攀附,实则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运筹帷幄给人信心希望,也不过是因为于他来说刚好是一枚有用的棋子。
她知道他一直都是如此,可真实听来,何其扎心。
沈洲听她这话怔了片刻,侧头回看她:“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知道宋南枝不喜被人跟着,遂那日之后便没再让人暗中跟着。只是她既然乘王府的马车去了宝斋,他先前却并未看见有马车停在宝斋附近。
宋南枝自也不会告诉他,为了隐瞒她去宝斋,她一直将马车停在了别处。如今见他并未私底下去查她,那原本想坦白的话,忽然又堵在了喉咙里。
“没去成,掌柜关门了。”
她也没必要事事与他坦白,她的宝斋与任何人都无关。
宋南枝屈膝往里走。她今日穿得是一件藕荷色襦裙,裙摆侧的沾弄到的墨点极为显眼,可她自宝斋出来便神情惝恍,并未发觉。
沈洲在后头略略扫了一眼,也不曾在意那墨色如何,只是觉得那背影腰身好像是瘦了。
今日晚膳瑞王妃安排在了东院,沈柯也来了,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用膳虽是头一回,却也很是融洽。
沈柯近来食欲很好,瑞王妃一边劝她夜里不能多食,一边又帮她添菜。回过头见宋南枝是没什么食欲勉强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问了一句:“你近来食欲不佳,可是哪里不适?”
宋南枝摇头:“可能是中午吃多了。”
瑞王妃道:“你那食量本就吃得少,哪来的吃多了。”
然后若有所思一阵,突然想到了什么,冒出一句:“是不是有了”
旁边寡言漠然的沈洲,听见此言,筷子忽然一滑,然后转头看向宋南枝的脸,又慢慢移至她的下腹。
沈柯也满脸惊讶,停下筷子,眨巴着眼地望向宋南枝。
因为下午沈洲与太子那些对话,宋南枝的心情一直不太好,眼下突然被大家这么瞧着,呆滞了一瞬,也莫名紧张起来。
但想起前几日才看过刘太医,又松了一口气,回说:“刘太医前日已经把过脉,应该是没有。”
瑞王妃点头,然后又说:“那我明日吩咐厨房多做一些可口的,你这脸都瘦了好些。”
宋南枝应好:“多谢母妃。”
沈柯撇撇嘴,略有些失望,嘟囔了一句:“我还以为我要升辈分了。”
被这么一问,沈洲又直看着她,宋南枝吃不下,又觉得有些尴尬,起身告退。
见她一走,沈洲也放下筷子,跟着出去了。
两人回到西院一路无言,本要自廊下分开,沈洲将她唤住:“若是王府事务太过操劳便与母妃说一声,让人顶了那些事。”
宋南枝说:“无妨。”她近来也并非是因为王府的事忧心。
然后两人都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们俩如今虽说已经同过了房,但其实与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都睡在自己的房,互不打扰。
所以怀孕这件事,宋南枝觉得暂时不合适,她应该要少与他接近,也不许他再近身。
房间熄了烛火,宋南枝躺在软榻上辗转难免。
也不是因为晚膳间的事,而是一直在想那日沈洲说的,宝斋与纪府有关就会有祸事。
她这几日每天都会去宝斋,提心吊胆的,怎么也静不下来,且又想不明白,可今日听见太子与沈洲的谈话,她方才知道那是何意。
朝中有人要针对太子,自然也会从太子身边的人下手,纪太傅如今虽不参与朝政,可纪护野却还任詹事一职,且与丁冉还有婚约在身。
若是他们寻个由头生事,她又该如何应对?
宋南枝心中一阵不安,又决计不会再寻沈洲帮忙,遂打算明日一早让安伯把宝斋先关闭歇一阵。
可她刚合眼入睡了一会儿,身后突然有人贴过来,伸手握住她的手腕,又搭在她的脉上。
这般粗鲁蛮横,除了沈洲还有谁。
宋南枝很不喜欢他这样:“前几日我生病方才见过刘太医,自然把过了脉,世子这是做什么?”
那夜她浑身怕冷,沈洲还来讥笑她身子不行,分明都看见了,竟还无故来探她的脉。
“你的话没几分可信任。”
沈洲早年学武也学过写几年医术切脉,眼下搭在指下的脉搏确实无异,复又躺回她的身后,手伸前搂过她,头埋在颈边:“睡吧,别折腾了。”
灼热的胸膛贴着她的后背,腰也被他的手搂的无法动弹,宋南枝挣扎了两下,放弃的闭了闭眼,“世子放心,我不会有身孕。”
他如此紧张又不信任,怕是担心的不行了。
可她话一说完,身后的人忽而僵了一瞬,似是想到了什么,眸色一凛:“你敢如此确定?”
宋南枝说:“是。”先前刘太医为她调理身子的时候时常提醒她,月事后什么时间段容易受孕,眼下她没有怀孕,也是同房的时间合不上的缘故。
可沈洲听她说完面色却随即转冷,不带任何温度,“你怎么敢?”
宋南枝被他问的有些莫名其妙,正满脸疑惑,下一瞬就被压在锦衾上,他似是有些不可置信:“你不惜嫁进王府,如今竟然敢喝避子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