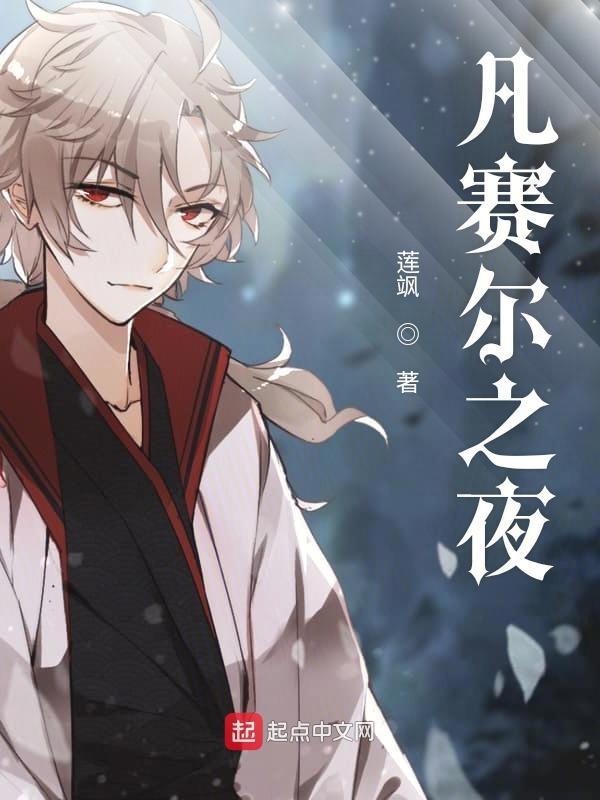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病娇侯爷的童养媳 > 第83章(第1页)
第83章(第1页)
接过太玄双手递过来的,早就已经供奉在佛前多日的朱砂笔。在少年的眉心轻轻落笔,一点朱砂落,魂灵就此安。
朱砂是供奉在佛前多日的朱砂,和朱砂的是他云缱的心头血……
人间帝王的心头血,只为护他魂灵安。
随安懒懒散散的靠在云缱的怀里,任由他给自己的眉心点朱砂。既然云缱觉得这般可以心安,他会无条件的配合。
禅院里。
一株已经度过百年春秋的桃树,此时枝头方才堪堪绽放满枝的春色。风吹过,落英缤纷。
树下,随安被云缱安置在摇椅上,正在慢悠悠的赏着这头的桃花,眉心的朱砂比这满树的桃色更加衬人。
不远处的廊下,笔墨纸砚已经全数,被林如还摆在自家陛下的手边。上好的宣纸,笔尖或轻或重,墨色浓淡相宜,寥寥几笔就已经在纸上勾勒出百年桃树,以及树下人。
随安不喜欢被人画,所以,上辈子他的画像简直就是少的可怜。仅有的那些,也全部都是云缱闲暇时亲手替他画的。
毕竟上辈子名声在外,也没几个人敢直视宁侯殿下玉颜的。所以也就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宁侯随安有着一张俊美的玉颜。
就如现在,仅仅不过是上辈子七八分的颜色,就已经被眉心那一点朱砂衬的颜色姣好。
佛门清净之地,张丕芝拎着自己仅剩的半坛子酒趴在墙头上,看禅院里那让他牙根疼的情景。果然,他就是没人疼的小可怜哦!
太玄法师带着小沙弥路过,对趴在墙头上,略显显眼的某人视而不见。
“小师叔……”小沙弥指指墙头有失体统的某人,一脸惊诧的看着视而不见的自家小师叔。
“阿弥陀佛,莫管莫问,这人就是一个祸害。”太玄教导身边的小沙弥,毕竟,这庸医要是撒泼打滚起来,他是收拾不了的。
“哦……”小沙弥似懂非懂,是不是就和师父说的,山下的女人是老虎一般。他不懂何意,但是,小沙弥很听话就是了。
张丕芝:我听见了!太玄,你一个出家人都是这么骗小孩子的吗?
说他是祸害,他祸害谁了。他明明是救死扶伤的好不好的,让太玄这么一说,好像他是什么打家劫舍的似的。
墙外纷扰扰不到墙内,躺椅上的少年已经昏昏欲睡,暖风花香熏人醉。云缱放下手里的笔,桌案上的画作已经完成。
慢步走到随安的身边蹲下,指腹细细描摹随安的眉眼。
“嗯?”
迷迷糊糊的随安侧头看云缱,双眸迷离在看到他的时候,满是依恋。云缱看着他笑的温柔缱绻,指尖刮了刮他的鼻尖。
“要好好的,你最重要。”
随安张嘴咬住他的指尖,不想这手指继续作怪扰他。云缱朗声大笑,笑的开心愉悦。
看的伺候着的林如还一阵热泪盈眶。
算了,他的随安从来就不是安分的,也不是怕事的。从前那般险境都是他陪着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如今不过是一些余孽而已,大权在握的他又怎么可能对付不了。
他会护着自己的心肝儿,他想在这风雨欲来的上京怎么搅和都可以。
世家这种东西,从来就是灭不干净的。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历经多代的簪缨世家,今朝不出,谁又说得准明朝如何……
风动?云动?
究竟是风起催云动,还是云动携风起?
在这上京城中是说不清谁是谁非的,不管是风惹的是非,亦或是云挑起的祸端……
最后的结局都不是他们可以说了算的……
宁园。
随安坐姿端正的听着时安絮絮叨叨的念叨,眼睫低垂,不想听,却又不能不听。
毕竟,他理亏在先。
这混小崽子,知道的他是去读书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出远门了。
远兮与赤兮皆是低着头,手里认认真真的替时安少爷收拾着笔墨。半点都不敢抬头看他们家殿下那称得上是生无可恋的脸,生怕自己忍不住笑出声,让殿下待会儿拿他们出气。
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就是昨儿。时安少爷下学回来,刚刚踏进院子的门,就看到他们殿下端着自己个儿不想吃的药膳,倒给了时安少爷养的貍奴儿吃……
那两只貍奴儿,是陛下从宫里的兽园专门替时安少爷挑的。都是顶好的,外头难得一见的珍品。
活蹦乱跳的貍奴儿可不是那些摆在房间里的花木,无知无觉。花木换了也就换了,可这两只貍奴儿,那可是时安少爷的小心尖尖。
若是被他们殿下喂出了什么毛病来,时安少爷可是要心疼的落泪珠儿的。
随安听着耳边时安的絮叨,心里却在翻来覆去的埋怨着,做久了帝王跟他都要耍心眼的某人。确实答应了他可以不用再喝药了,也把张丕芝那庸医扔去了万安寺。
但是,他竟然转头又派了善做药膳的御厨,塞进了他的宁园。整日里变着法的做了满桌的药膳,不仅仅是一日三餐,从茶水到点心蜜饯,就没有那群御厨做不出来的……
简直丧心病狂!
终于送走了絮叨了一早上的时安小少年,随安摸着怀里貍奴儿软滑的皮毛,慢慢悠悠吐了一口气。
“殿下。”
“这上京城是风起了?还是云动了?”随安捏着貍奴儿温温软软的软垫,眉眼低垂逗着貍奴儿。
“尚不知,只是探知到有人在打听殿下您的消息。”
闻言,随安眼底闪过一抹意味不明的晦暗。自他醒来至今,甚少出宁园,仅有的几次,不过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