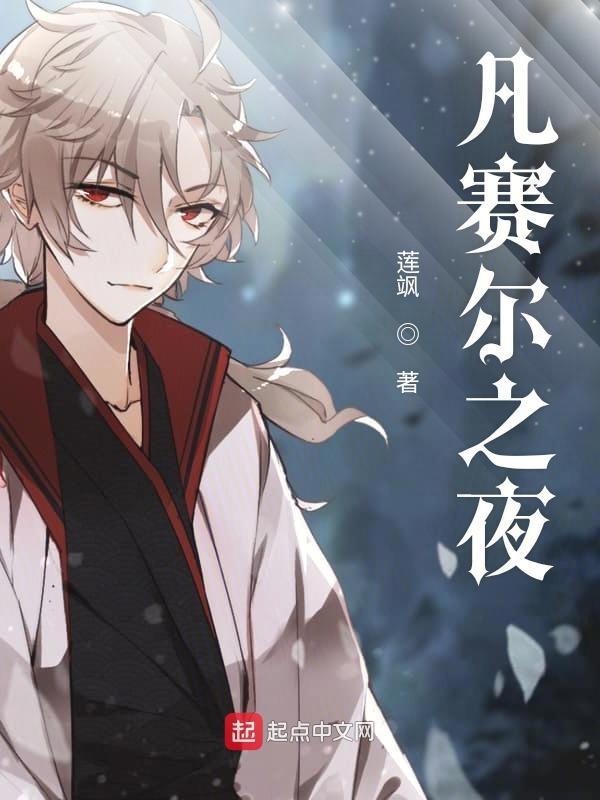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他的缪斯免费阅读 > 第40章(第1页)
第40章(第1页)
徐妈惯会察言观色,从不多说什么话;闻星更是安静,为避免打扰沈流云作画,连琴都不怎么练了。
偌大的房子里分明有三个人,却呈现出一副毫无人气的阴沉。
至于沈流云,他每天都进入工作间,花大量的时间对着画架枯坐,地上堆满废弃的画纸团,大有将他淹没其中的趋势。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外出写生,他早在两年前就进行过多次尝试,专往人烟稀少的地方钻,全国各地几乎跑了个遍。一无所获后又往国外飞,哪里景色美就往哪里去。
可哪怕是站在曾经令他灵思泉涌的地方,他的大脑始终是一潭死水,苍白而无力。
沈流云无比明确地认识到,他已然成了一片濒临枯竭的湖泊,曾经引以为傲的天赋不知何时早就悄然离他而去。
闻星极少出门,亦不过问沈流云的作画结果,整日专心伺弄院子里的花草。
有时候,沈流云在画架前待得烦了,起身想去窗边抽根烟,推开窗往下看,就能瞧见花园里闻星忙碌的身影。
临近冬日,天气逐渐转凉,花园里大部分的花都已过了花期,一眼望去只能看见深深浅浅的绿以及空荡荡的枝条,很是萧索。
视线内的人忽然蹲下,使得原本被他的身躯所遮挡住的一丛淡紫色花株显露出来,擦过他的小腿,往上攀爬般倚靠,是玫瑰鼠尾草。
当初闻星种下它时,告诉过沈流云,这是一种耐寒且坚韧的植物,彼时的他不以为意。
如今瞧见大多数花凋零、枯败,唯有此花仍在生长,方觉其不凡。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菲利斯的爱。”闻星那时说过的话似乎依稀还能听见。
寂静无声、坚韧难折的爱。
闻星抬起头时,无意与沈流云的视线相对,微微一愣,而后朝他展开一抹浅淡的笑。
他身后的小型喷泉在这时涌出一大股水,哗啦啦地落下。
沈流云奇异般地安静下来,呼吸间似乎闻到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花香,喷泉的水也随之浇在他的心上,湿润着泡胀。
恍惚间,他意识到,每当他处在焦躁、忧郁的时刻,都想要住进闻星的眼睛里,以此获得短暂的休憩。
无限制的包容,无额度的爱意,他被如此慷慨地给予。
从工作间出来时,沈流云瞧见徐妈将医药箱拿了出来,眉头一皱,看向沙发上的闻星,“怎么了?”
闻星原本低着头准备把裤腿挽起来,听到沈流云的声音,挽了一半的裤腿又放下去,抬起头回答:“在花园里不小心被刮了一下而已,不是什么大事。”
有的花草尖锐锋利,一时不察便会刮伤。此事在过去屡见不鲜,但闻星的体质特殊,极易留疤,沈流云认为不该草率对待,还是朝这边走过来。
“给我看看。”沈流云在闻星的面前蹲下,徐妈识相地将医药箱放在一旁。
可就在沈流云的手即将碰到闻星的裤腿时,那条腿往边上躲了一下。
闻星抿着唇,有点冷淡地看着他,“没什么好看的。”
沈流云的眉头拢起来,很不解,“你伤到了,我看一眼都不行?”
“小伤而已,徐妈帮我弄一下就好了。”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太过强硬,闻星略有缓和,却依然于事无补。
沈流云不说话,就蹲在边上没动,目光沉沉地看着闻星,丝毫不打算退让。
最后还是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个僵局。
沈流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震动的手机,走到边上去接电话。
趁他接电话的间隙,闻星将裤腿挽了起来,让徐妈帮忙处理小腿上那条鲜红的划痕。
面积不大,痛感轻微。
然而闻星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一种似乎痛得狠了的茫然,雾蒙蒙的。
因为伤口很小,徐妈很快便帮闻星处理好了伤口。
闻星轻声说了句谢谢,将裤腿放下去,抬起头时看见沈流云打完了电话朝这边走来。
他看见沈流云的目光在自己和徐妈的身上转了转,最后落在徐妈身上,惜字如金地没有开口,仅用眼神示意。
徐妈心领神会,连忙答话:“确实是小伤,稍微消了下毒,贴了个创口贴,之后少碰水很快就能好。”
沈流云勉强满意,目光转回来,“连霂叫我过去聚一聚,晚饭我就不在家里吃了。”
像是出门前交代去向的一句话,但说得太生疏,闻星听在耳朵里,觉得他这话说给佣人也并不违和,因而没有回应。
说话的人看上去亦没有等他回应的意思,不愿再在此处多待一样,匆匆拿上钥匙便出了门。
家里立时安静下来。
闻星静坐了会儿,才对明显不知所措的徐妈勉强地笑笑:“徐妈,给我倒杯咖啡吧。”
“欸,我去给您倒。”徐妈进了厨房,不多时,端出来一杯咖啡。
闻星接过咖啡喝了一口,眉头轻轻皱起,太甜了。
他放下杯子,诧异地看向很少在这方面出错的徐妈,“有点甜了,这是加了多少糖?”
他喝咖啡的喜好是只加奶不加糖,沈流云则是不加奶也不加糖,说这样才能喝出豆子最本真的味道,家中的糖例来都是为了客人准备的,按理说不会弄错。
闻星原以为只是一次偶然的工作失误,没料到徐妈拍了下大腿,懊恼地吐出一句:“我这脑子真是,不小心将您和另一位先生的喜好搞混了。”
她有将雇主的喜好记在本子上的习惯,重新回到这边做事前特意温习过一遍,不料却弄错了对象。
“另一位先生?”最近这段时间唯一来过家里做客的就只有关泓奕,闻星因此推测,“是上次那位关先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