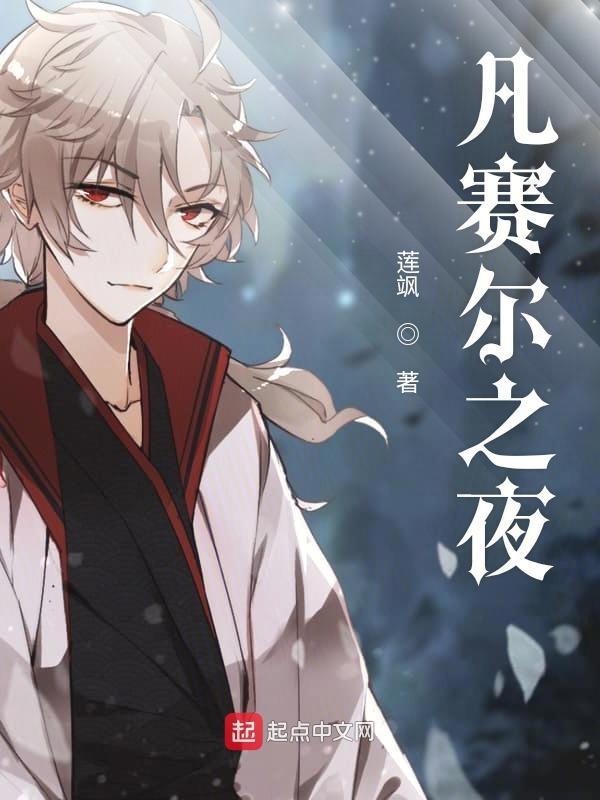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明我长相忆 > 第92章(第1页)
第92章(第1页)
魏慎荣愤愤道:“治水本就是一件慢事……”又被李令抒打断:“可是殿下也认同这方提案。”
他说起杨擅,忽想起一件事,对站在四人远方的东宫护卫喊道:“王卫长!殿下与宋大王在后头,马上也要到了。他们两位不习惯走山路,你去帮一帮。”
东宫护卫吱唔一声,急急忙忙往山下跑,迷茫地望着三方山路。李令抒道:“我带你过去。”扶着石头一路下到护卫身边,毛公裘见状向魏慎荣一揖,道:“魏使才到崖口,请先往四下观察。我们去引殿下过来,稍后再详谈治水之案。”
他话虽说得客气,辛时和魏慎荣却知道,在杨擅的授意下治水方案已然确定。辛时倒没太多想法,不知思考着什麽出神,魏慎荣却在对面离去后越发不平,对着辛时也不避讳,一股脑倾倒怨气:“一个挖石料的,什麽都不懂,这不仗势欺人吗,哪有这样的!殿下也是,跟出来闹着玩也就罢了,川水是关乎一整个州的大事,魏某认识的那麽多同僚理过的那麽多前人经验,没有哪个说会往地上造河的,这不就像身上长了脓包,不但不挑破,还越养越大吗?”
辛时忍不住笑起来,听魏慎荣言语不妥,及时安慰道:“魏公慎言,东宫为大,不可妄议人主。陛下在神都远候消息,圣心焦灼,当务之急是止住涝害,越快越好,东宫之策实为上举。你有心利民,何不回去后上禀神后,待今年农閑时征招民力疏浚河道,也算为后世解决水患之忧。”
魏慎荣这才慢慢地消气,回味辛时的话,承认他说的不无道理。他还是不能完全认同杨擅的做法,但辛时与皇后关系亲密,更擅长揣摩上心,便听从他的建议:“也是,也是,这两件事不沖突。但我说殿下嘛……太积极了,坐镇中方就好了,跑来参与治事,好心帮倒忙。”
从心底里,辛时很赞同魏慎荣的话。可臣子怎麽能说主上的错?就像太子与神后,无论再怎麽知道母子两人政见不和,在一切可能时辛时都只尽力帮两人弥补关系的份,魏慎荣不懂这一点,他只好又劝:“殿下尚年轻,心有鸿图,凡事亲为乃明君之象。他或有不周到处,我们再替他补足,这是人臣之道,我们为人臣子者,不过就是替主上尽这一份事后之力。”
好容易安抚完喋喋不休的魏慎荣,转头时,再次看到高地之下浪滔滚滚的灵水。近水的农户早已被迁走,单调的浑浊河流一如数个时辰前,裹挟着泥沙依旧在肆意横流,水面被风吹出阵阵波纹,叫人分不清哪里是曾经的稻田、哪里又是真正的河床。
辛时松一口气,然而被魏慎荣打断前心底腾现的奇异不安,此时又如泥土中的洪水一般隐隐漫上来。回想最近发生的种种事迹,以谶讳之言论实在不是什麽好的迹象,仿佛一场巨大灾异的先兆。杨氏天子手握朝政也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若宗庙受损……天命又该落在谁的身上?
风将浪抛得更急,呼啸至崖口催生出令人站立不稳的假象,辛时不得不拉紧身上衣带。隐约闻得身后有人声,回过头,便见是去东肴山勘察的杨擅与杨修元终于到场,太子殿下亲热地挽住堂兄弟正说道着什麽,指点远处江山。杨修元碍于对方颜面频频回应,表情却略有不耐,一擡头对上辛时的视线,不自觉露出明晃晃的笑容。
从城外勘察回来,杨擅第二日与三位治水主理官员议论片刻,很快确定下最后方针,毫无意外跟着他的思路。这头事了,他又立刻投身回祭祖的事情中,待到两日之后,衆人一道去观礼。
大周宗庙之仪承袭前朝,辛时小时候见过,在宫中读过记载,眼下与记忆中大差不差,更为隆重且漫长。先人衣冠被一排排请出绕城周游,一路载歌载舞、烹羊宰牛,直到日落时分才又重被请入庙堂,诸灵归位。
辛时回到住处,已是深夜时分,甩掉外袍往榻上一趟,长舒一口气,只觉得脚底又酸又胀,浑身骨头像要散架一样。这几天又是爬山又是祭祀,差不多要到体力的极限,反观杨擅祭典结束时依旧一副神采奕奕的模样,能当天子的果然都不是常人。
正想着,房侧窗子被轻之又轻地扣动两下。辛时默默在“天子”后面再加上一条“天子的宗亲”,懒得翻身下榻,一手揉着膝侧穴位,一手抽出颈下枕头往窗框砸去,道:“白天站得不够多,晚上还有精力夜探别院。”
枕头磕在木质格栅上,有气无力地掉落地边。“吱呀”一声,杨修元推开床扇探头进来,两只手挂在台上,很熟练地翻身越入室内。
他顺手捞起枕头,道:“祖庙我是第一次来,瞧着新鲜,倒没觉得累。”
辛时道:“神都南郊也有宗庙,你从前进京时,应当见过庙祭的吧?”
杨修元道:“祖庙是祖庙,宗庙是宗庙,这不一样。宗庙从前家里也有,每至晦朔热闹非凡,我还和你偷偷溜进去玩过,祖庙真是第一次来。”
辛时笑他:“太子是为祭告先人,到你这却变成看热闹。某人溜进宗庙的结果别还要我提醒他,差点被揍得屁股开花。”
语毕杨修元走近榻前。他给枕头拍了一路灰,眼见还是没拍干净,干脆往地上一扔,挤上榻去:“阿爹阿娘不舍得揍你,当然只能揍我,反正我在家里就是最淘气的惹事精。”
辛时道:“那是因为叔父叔母宠你。他们不罚我,怕我心生间隙。”
杨修元努努嘴,不置可否,只侧身将手臂整在头下看他。辛时回望杨修元,也许是因为提到了小时候的事,突然觉得有点神奇的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