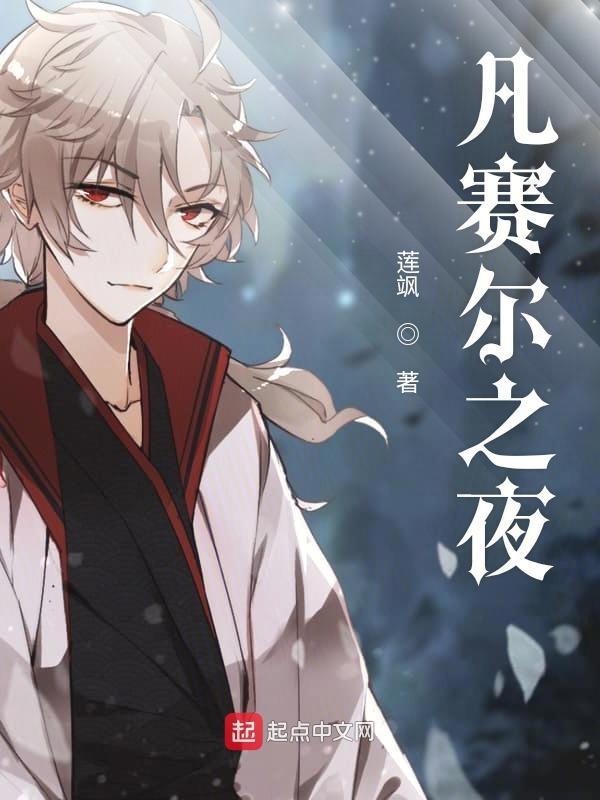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黄金墟狂丝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汪海洋认出郑新亭来了,微微笑,算是打招呼。郑新亭朝他点头,说你也来照相啊,汪海洋说来取我爸的遗照。郑新亭沉默片刻,说了句节哀。汪海洋没讲话,跟老板进里间。不多会儿,他出来了,怀里捧着老头的新遗像。
黑白照,显得眼神很凶,脸瘦削,颧骨高高戳起。他总觉得旧的那张太陌生,是他爸二十三岁刚进工厂时照的。他那时候才两岁,对他爸完全没印象。
翻来覆去地看,现在这张蛮好,已经五十多了,他熟悉。相框也挺漂亮,雕花盘龙,镶两道金边,是用油漆描的。
汪海洋站在门口,打算抽根烟再走,发现没带打火机,问郑新亭借,郑新亭说我不抽烟。
郑知着看着他们,掏口袋,摸出一只红色的打火机,上面有字,印着吉祥如意。是他从方老二那里顺的,用来点小炮玩。打着,还会响音乐。汪海洋觉得耳熟,好像是致爱丽丝。挺动听,让人想流泪。
风大,抬手拢了下火,汪海洋抿着烟跟郑知着说,谢谢你啊帅哥。
不客气,郑知着豪爽地摆手。他嗒嗒按着打火机,心不在焉,眼神被对面新出炉的鸡蛋糕吸引。郑新亭给郑知着五块钱,让他去买一兜子。郑知着高兴地跑去了,随手把打火机塞给郑新亭。
阳光呈现难得的灿烂,汪海洋眯起眼睛。对面房顶立了两只鸽子,白羽毛,红眼如玛瑙,在敏锐地捕捉到人注视的目光之后它们便立即振翅而飞。视线又落空,只剩无边的天幕。
汪海洋抽烟,跟郑新亭说,我爸昨天没的,上吊自杀。工厂倒闭之后连医疗补助都发不出来,老头等不得了。他在化工厂干一辈子,退休就得肝癌,没钱治,把我妈熬死了。去厂里要钱,被人赶出来,鞋也没了一只。我爸跟他们喊,说他连续十年都是厂里的劳模,工人协会的副主席还给他发过奖章。没人搭理他,厂子都快空了。周叔跟我说,我爸昨天就一直在找鞋,找到半夜都没找见。汪海洋顿了顿才又继续说,我爸他没认多少字,死前给我写了封信,我看不懂,大概还是劝我别做同性恋。他老替我操心,现在好了,死了就不用见到我了。
汪海洋流眼泪,烟烧到头烫了手,这让他想到火葬场的炼人炉。他爸烧了个把小时才算完,盒挺轻,没什么分量。郑新亭说我知道,我爸死的时候是我捧的骨灰盒。我爸一百五十多斤,最后就剩这么一点,我不敢信,忍不住打开盖子看,都是灰白的粗颗粒。我当时想,原来这就是骨灰,我爸的骨灰。然后,我就被我哥揍了,那是我哥唯一一次揍我。
“小叔。”郑知着胳膊挎只塑料袋子从街对面飞奔过来,正吃鸡蛋糕,嘴里黏糊糊甜蜜蜜。
“好吃吗?”郑新亭笑着问,郑知着亲热地喂给他一个。
汪海洋扔掉烟头,说我该走了。郑新亭说,再见。再见再见,郑知着学着小叔的腔调,挥手告别。他看上去很快乐,毫无分别的忧伤。
汪海洋转身,又回头,跟郑新亭说谢谢,刚才冒昧了,你就当听个故事,别记着。郑新亭说,好。
汪海洋走了,回他那个毫无生气的家。家里没有一个人,因为背阴,所以屋内昏暗寒冷。他慢慢地走,想多晒一会儿太阳。六甲的冬季潮湿多雨,今天难得晴暖。他把相框翻过来,照片朝上,说爸你也晒晒,省得骨头疼。
街道很安静,郑知着站在马路牙子上吃鸡蛋糕,一口三个,塞得两腮鼓出。郑新亭说该回家了,他眯着眼看太阳,问回家干嘛。
无非是看电视,打游戏机,听半导体,郑知着觉得无趣,可在外面闲逛也一样无趣。
他心智低下,愚蠢,这辈子注定无所作为,只需要享受单纯的快乐,经历一点不能明了的悲伤,然后再迅速忘掉。况且,他那么年轻,有大把时间可以用来浪费,无需珍贵。在二十岁的年纪,什么都不做其实是被允许的。
郑新亭替郑知着出谋划策,说去陪你奶搓麻将,或者跟着方瑞军出摊。郑知着摇头,他上过牌桌,最后把局面搞得乌烟瘴气,输掉好几个钢镚儿,那天就没能去小卖部买零嘴吃。
至于跟方瑞军算命照相,他也去过。挺倒霉,电脑不幸坏了,方瑞军给他戴上墨镜,让他伸出指头翻来覆去地掐。郑知着掐得手酸,听方瑞军跟马四兰在旁边胡言乱语,说什么大罗神仙下凡,茅山掌门出山。郑知着坐不住,脚一伸就把桌子踹了。不是有意的,但方瑞军一气之下就把他拎回了家。
郑知着没什么朋友,小铁锤总是在码头打弹珠,李飞忙着吹气球,他不知道能跟谁待在一起。只有小叔,他的小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陪他闲逛,跟他聊天吃饭睡觉的人。小叔宽容他的暴躁跟有意无意的错误,小叔给他买好吃的,填饱他的胃跟渴望,小叔会跟他亲嘴,令他体会到别人所说的恋爱的甜美。郑知着想,他这辈子只能跟小叔过,也只想跟小叔过。
这种想法未免有点浪漫过头了,但郑知着不懂,对现实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人生可以过得很轻易,无非是用力哭跟用力爱。
郑新亭带着郑知着回家,整个下午,他们什么都没干,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郑新亭看书,郑知着靠着他打瞌睡。大黑狗摇着尾巴来回走,警惕地巡逻,在鸡经过时一跃而上,蹿起两米高。
郑知着被惊醒了,抬头看天,已经擦黑。他一下就搂住了郑新亭的腰,说小叔到晚上了。
郑新亭没反应过来,还在认真计算数学题。郑知着掰过他的脑袋,狠狠亲下嘴,重复道,小叔,到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