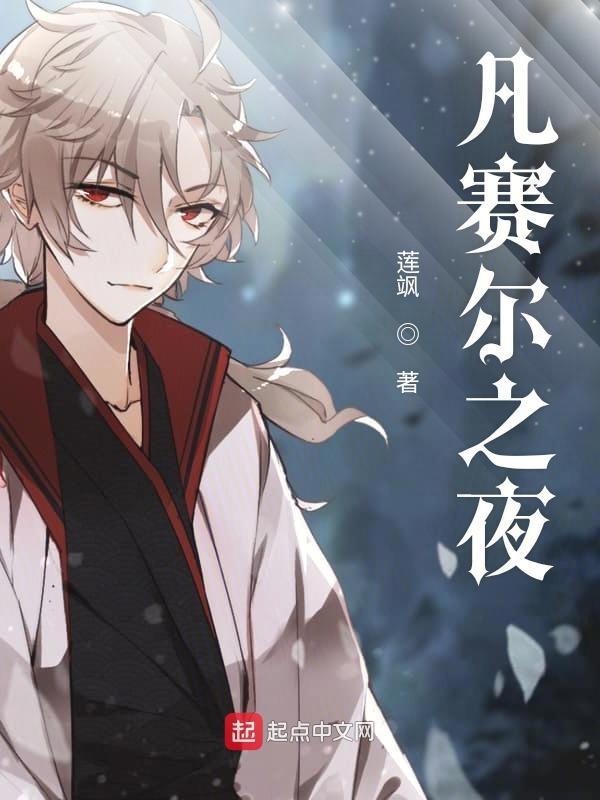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你崩人设啦长佩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疼,太特么地疼了。
时城眉头锁得更紧,他答非所问,“伤到哪了?”
夏清破罐子破摔,“屁股,脚……好像崴了。”
时城知道自己使力不小,他把差点儿散架的书包扔在一边,蹲下来伸手。
“啊,别碰,啊啊啊!”夏清捂着嘴小声尖叫。
时城无奈,“我还没碰到呢。”不过,肉眼可见,夏清露出的脚踝隐隐约约是肿了一点。
“去医务室还是直接去医院?”他问。
夏清从懵b的大脑里勉强扯出一丝理智来,医务室的老师古板又麻烦,一定会前前后后问清楚受伤的细节。如果去医院的话,要跟老师请病假,弄得人尽皆知,不说别人,就高珩那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劲,他可不想应付。而且,他小学的时候崴过脚,保姆在夏正阳的远程交代之下,带他去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又是拍片又是理疗的,也没见得有多好用。那次他伤得严重,半个多月才能下地正常走路。而不久之后,高珩也同病相怜地崴了另外一只脚,人家啥治疗也没做,好的比他还快。
高珩笑话他缺钙,为这事儿,两人绝交了一个礼拜。
“都不去。”夏清干脆拒绝。
时城的目光泛着疏离,好像在面对一团扯不掉的麻烦,“那怎么办?”
“你送我回家。”
时城沉默片刻,也不多话,“行。”
他起身,“需要我去帮你拿书包吗?”
夏清还在低头试探着摸自己的脚踝,不敢下手,戳戳点点,哼哼唧唧。
“不用。”他说,“我作业都写完了,没什么要带回去的,今晚摆烂。”他掏出手机,给高珩发信息,“找人给我晚自习请个假就行了。”
让时城去给他取书包的话,他怕跌破全班的眼镜。
他是学校为数不多的走读生,晚自习早退班主任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太跟他较真。
时城仿佛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得已随口一问,夏清说什么,他不追问也不反对。
“能走吗?”他推入下一道程序。
夏清不可思议地抬头,“你说呢??!!”
时城微不可查地吞了口唾液,语气不耐,“我扶你?”
夏清用一种谴责不负责任的渣男似的目光瞪他。
“你说怎么办?”时城被打败了。
夏清理所当然地,颐指气使地,屈尊降贵地吩咐道,“你背我。”
深秋的傍晚,天暗得早。再加上这座老工业县城原本灰突突的基调,不到七点钟的时间,天地一片黯然。
夏清趴在时城的背上,时城一只手勾着书包,另一只手虚虚地托着他没受伤的那条腿,夏清不想掉下去的话,只能自己手上腿上使力,尽量趴得老实。
好在,时城肩背宽阔,步子迈得缓而稳,他在人家背上保持平衡倒也不算很费劲。夏清时不时调整着两只手揽在时城脖子上的角度,他一动,时城就停下一步,但也不会问什么。待他调节好,再继续迈步。几个来回之后,夏清的小腿从紧张的绷直到一点点晃悠起来。
这一路,夏清在高出习惯视角的高度上新鲜地东张西望,除了在回答门卫大爷问话的时候稍显心虚之外,其他时间莫名地踏实,还有一丝丝不为人道的窃喜。
走到小区门口,遇到两个拎着安全帽的工人。其中一个浑身烟尘混着明显老烟民气味的大哥看到他们,走了两步凑近来,诧异地问时城,“小孩儿,今晚交班时间过了,你小子怎么还没去,不怕工头骂啊?”
时城闷声,“就去了。”
一问一答,短短两句,让夏清咂摸出不少线索来。原来时城打工的地方是他们小区后边的工地,美其名曰是学府苑的二期,其实就是原来的开发商看他们这个小区房价飙升眼红了,给后边烂尾楼旧房子做的翻新工程。时城上的是夜班,工头会骂人,工作氛围一定不咋地。还有,“小孩儿”这个词他怎么着都和这位人高马大的酷哥联系不到一起,听着怪搞笑的。
他这么暗自思忖着,竟然真的就笑出了声,等意识到,又咳了两下,欲盖弥彰地自言自语,“都是烟味儿,难闻死了。”
时城没什么反应,夏清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
夏清小脑袋瓜里杂七杂八地思索着出神,下意识将头枕在时城肩上,鼻尖恢复萦绕的清爽皂角气息。以至于,顺着他的指挥到了家门口开了密码锁,时城已经站了半分钟,他才迟钝地爬下来。
时城将自己的书包扔在门外边,搀着夏清进门。夏清其实早就发现,自己受的伤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当时是被砸懵了,又摔得晕头转向,陡然的惊惧、疼痛、委屈一起袭来,他才会有那么大的情绪反应。刚才他在一荡一荡的晃腿中已经确认,脚崴的不严重。至于其他地方,估计也就是个擦伤的程度。
夏清煞有介事地一颠一颠,扭是真扭,就算没那么糟糕也不能立马承认。
时城把他扶到餐厅桌边的椅子上坐下。
夏清扶着桌子,低头别别扭扭地,“那个,谢了哈,虽然是你让我受伤的,但,内什么……算是我也有错……扯平是肯定扯不平的,不过你要是着急去……”
他话没说完,只听到“砰”的关门声。
夏清猛地抬头,哪还有人影。
“……”他目瞪口呆,好半天,抓起桌上的杯子……又放下,换了一包纸巾使出吃奶的劲儿朝大门上甩过去。
“算我倒霉!”夏少爷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
夏清灌下大半壶凉白开,才堪堪压下心头噼里啪啦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