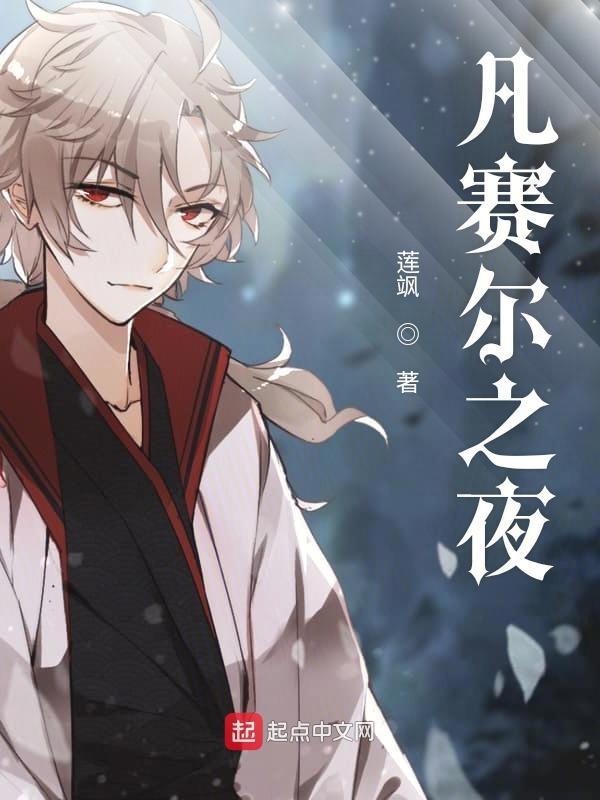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他的缪斯许奕免费阅读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艺术品
一截带着红星的烟灰不慎落下,尽管沈流云及时抬脚碾灭,那红星还是在地毯上烫出了个不可挽回的焦黑窟窿。
盯着那个新诞生的窟窿看了片刻,沈流云烦躁地将剩下的半截香烟也给掐灭了,随手扔进边上的颜料盒里。而那个被他临时用来充当烟灰缸的颜料盒,里面的分格已然满满当当地塞了五六个烟头。
沈流云的烟龄不算长,从前这东西在他这里只起到装腔作势的用处,近几年因为画不出画的次数增多,烟抽得比从前凶了不少,等有意识时已经不知持续这种情况多久了。
由于沈流云个人对作画环境的严苛要求,工作间里基本上只有画具和画作,如今连画作都没摆几幅,更加显得空荡。
他脚下这条刚被烧坏的摩洛哥风格地毯是偌大空间里唯一的装饰品,赠送人是闻星,三年前买于菲斯街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历经约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后送达他的手中。
闻星素来钟爱古典乐,对摩洛哥一年一度举办的菲斯音乐节心弛神往。该音乐节结合了古典乐、民族乐与圣乐,极富盛名。
三年前,闻星终于有机会飞往摩洛哥参加了一次,并带回了这条地毯作为礼物送给沈流云。
临行前,沈流云看着收拾行李的闻星,最后确认了一遍,“真的不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闻星停下收拾东西的动作,抬起头诚恳地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音乐,我不介意你陪我一起前往。但如果你只是为了陪我,我想没有这种必要。”
闻星对音乐的热爱令他容不得任何人对音乐有半点亵渎,哪怕对方是自己的恋人也不行,这一点沈流云在与闻星交往之前就有所知悉。
只因闻星曾痛斥过某一任交往对象的恶劣行径:那人为了投他所好,邀请他一起去听音乐会,却在听音乐会时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睡觉。闻星对此忍无可忍,一走出音乐厅就提出了分手。
沈流云听得笑起来,说了句,确实很不尊重人。
“不是尊重的问题。”闻星条理清晰地反驳,“我并不会要求我的恋人像我一样喜欢音乐,他甚至可以不喜欢音乐,但是他不可以为了迁就我而假装自己喜欢音乐。你难道不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吗?”
“我讨厌欺骗。”闻星最后皱着眉,这样总结。欺骗。
这两个字如一记警钟在沈流云的脑海里重重敲响,令他不得不直视面前那幅已经完工的画作,那由谎言堆砌的杰作。
沈流云抬起手,在即将碰到那幅画时停住,改用目光自上而下地扫过整幅画。
画的左上角是光的,闻星的下颌。
——“画完了吗?”
——“还没有。”
这是第三个谎言。
画的中央是光的中心,闻星的脖颈。
——“我不在你身边,你就画不出来了吗?”
——“怎么会?”
这是第二个谎言。
画的右下角是光的暗部,闻星的肩部。
——“沈流云,你在画我吗?”
——“不是。”
这是第一个谎言。
千百种情绪在心中齐齐翻涌,于沈流云的眸底汇成一片躁动的汪洋,促使他突然之间疯了一样,愤愤抓起边上的刮刀就扬手朝着画布划去。
可就在刮刀将要落下之际,他的脑海里忽然晃过闻星将地毯送给他时的情形——闻星抱着这条色彩艳丽、图案繁复的地毯噔噔噔跑上楼,对沈流云粲然一笑:“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没等沈流云答话,就听闻星绘声绘色地讲述起他是如何在街边的小店一眼相中了这条地毯。
“我当时一看到这条地毯,就觉得它非常适合你。它跟你的画一样,明亮鲜艳,富有生命力。”闻星迫不及待地想要向沈流云展示这条地毯是何等漂亮,将其在地面上完全摊开,维持着半蹲的动作仰起头来,问他好不好看。
沈流云垂着眼,对上闻星的双眸,轻易就从中望见属于自己的小小倒影。
他顿时惊觉,闻星此刻的姿态宛若朝圣,一如这世间的许许多多人那般,钦佩他的艺术天赋,爱慕他的天才光环。
长久以来,都有人说沈流云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就连沈流云自己也认同这种说法。
艺术这条道路,努力决定了你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多久,但天赋则决定了你最终能到达什么位置,冰冷又残酷。
沈流云于绘画上的天赋就像是上帝的恩赐,令他能早早地领先于旁人,站到金字塔的顶端,任旁人如何努力追赶也难以企及。
这些年来,他一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天赋带来的便利,未曾想,有一天上帝会收回他的恩赐。
“咚”的一声,刮刀掉在地毯上,发出微弱而沉闷的声响。
沈流云瘫坐于地,面上是前所未有的颓丧,目光缓缓上移,看向那幅完好无损的画作,旭日绚烂的光芒如有实质般灼痛他的双眼,自眼尾迸出火苗,烈火连天。
他终是在这一晚认清了自己的内心所想:他宁愿欺骗闻星,也不愿闻星对他失望。
考虑到闻星睡眠不好,沈流云怕半夜回去睡把人吵醒,客房又都在楼下,他懒得下楼,便干脆在工作间的沙发椅上将就了一晚。
工作间隔音好,还拉着厚重的窗帘,外面的光半点都透不进来,让沈流云这一觉直接睡了个天昏地暗,临近下午四点才悠悠转醒。
他从前也有过半夜画画最后宿在工作间的情况,闻星似乎对此见怪不怪,消息框干干净净,没留下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