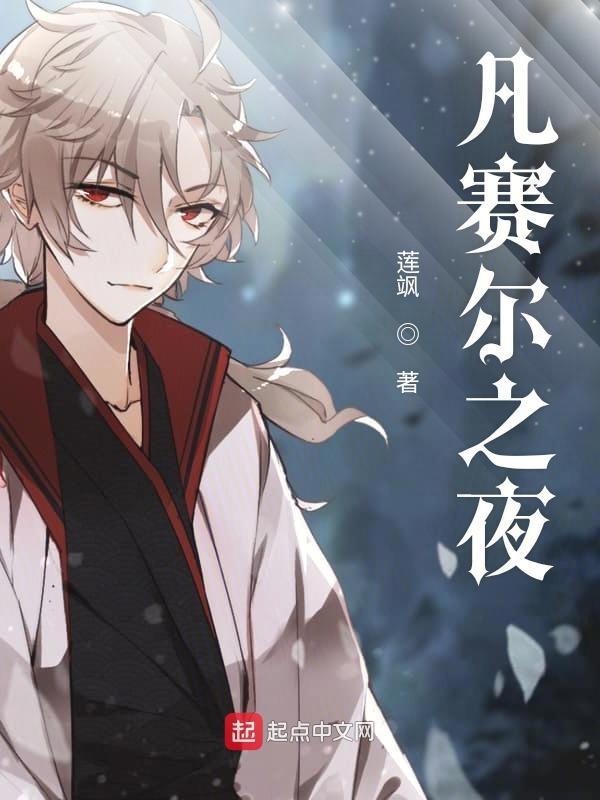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心机是什么意思啊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你没事吧!”
“天哪,怎么伤成这样?!”关怀的声音围绕在曾耀身边,没人搭理涂抑,顶多刺去一抹责备的神色。
只有木棉还站在门边,远远地看着他,待他也转过头发现木棉的时候,刚才挥拳时凶狠的表情立刻变为委屈模样,让木棉看到了他嘴角的伤势。
木棉见状,冰冷的表情果真开始动容,他走到涂抑面前,抬头端详他的伤。嘴角青紫交错,正微微发肿,比起曾耀的惨状虽是不值一提,可木棉心里还是不断漫起某种绵密的刺痛。
“你们把曾学长送医务室去,费用记在我头上。”木棉吩咐完,转而对涂抑说,“你,跟我过来。”
涂抑这时已完全丢失了打架时那强势的气焰,耸眉搭眼的像只犯错的大狗,亦步亦趋跟在木棉身后走路,蓬松的卷发轻轻颠动,看起来相当温良无害。
木棉将他带往没人在的办公室,关门落锁,这才直视他:“为什么打人?”
涂抑垂落头颅,半晌没动静。
木棉面色便又冷下几度:“你一个刚入社的新生,能和前辈闹什么不得了的矛盾需要动手?曾耀学长性格那么好,被你揍成那样,你这是在欺负人。”
“因为他欺负你。”忽然,涂抑开口,因为垂头,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什么?”木棉不解地盯着他。
涂抑猛地抬头,眼中有一丝恨意:“那个名单是他换的。”
木棉倍感吃惊:“你看到了?”
谁料涂抑摇头:“没有。”
“那是他主动告诉你的?”
涂抑:“也没有。”
木棉:“那你怎么知道名单是他换的?”
涂抑:“因为那天就只有他在活动室里,名单放在桌子上,他随时都可以动手。”
“涂抑。”木棉叫住他,“你的推测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前提——那份名单确定人为掉包过。可是你怎么确定是那样,而不是我自己出了纰漏呢?”
涂抑坚定地说:“学长没有把名单弄错。”
“你怎么能确定?”木棉嘴角绷紧了,“那天我没有听你的建议,没有进行最后的检查。”
涂抑那双漆黑的眼珠牢牢圈住了木棉:“因为学长那天已经提前检查过,我相信学长,学长说没问题那就一定没问题,名单一定被别人动了手脚才会这样。”
“你”木棉被他眼睛里坚定不移的信任撞得惊心,明明是那么感情用事的一番话,但木棉却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或者说他内心不想反驳,不想失去这一份只因为他才诞生的信任。
片刻的失语之后,他重新开口:“如果真像你说的,曾耀学长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涂抑瞬息间暗了暗面色:“我会盯着他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木棉没想到他是这个反应,“算了,你嘴角那伤也需要处理,走吧。”
这次涂抑没乖乖跟着他,立在原地说:“现在去医务室岂不是要碰见曾耀?”
“碰见就碰见,之后都是一个社团的,你没必要对他那么大敌意。”
“我不。”涂抑罕见地固执起来。
木棉更是罕见的耐心十足,没有立刻丢下他不管:“那你想怎样?”
涂抑抿了抿嘴,又搓了搓脚板,试试探探地开口:“我想学长帮我涂药。”
木棉很惊叹自己竟然没有让他滚,脑子里一瞬间闪过很多涂抑为他做过的事,甚至连此刻受伤也是为了他,心里软了,态度也就柔和些。
办公室倒是备有医药箱,木棉将其取出,找到外伤药膏和棉签。转身时,涂抑已经乖乖坐在椅子上等候,这是属于副社长的个人办公室,椅子只有一把,木棉在棉签上挤好药准备躬身擦拭,涂抑却想让出座位:“学长你坐吧。”
“别动。”木棉制止他,“哪有让伤员站着的道理?”
“可是——”
木棉用眼神逼退他的反抗,用棉签上的药在他的伤处轻轻涂抹一层,待换了新的棉签准备再涂一次时,就听见涂抑说:“学长,我伸手了。”
顿觉腰间一紧,那人竟抱着腰把他端上桌子。
“你!”木棉大惊失色。
“隔着衣服,没有碰到学长的皮肤。”涂抑已经掌握了接触木棉的良方,接着将椅子滑过来,分开木棉的双蹆,双手搁在桌上,虚环着木棉的腰。
他的脸恰好停在木棉手边:“这个高度刚刚好。”
这是十分越界的距离,太过亲密,姿势更是说不出的微妙。木棉的取向使他对大褪非常敏感,涂抑自然地分开它们,就留在它们之间。
心脏扑腾了几下,他竭力保持冷静,专注涂抹药膏。涂抑一脸正直单纯,似乎这举动没有深意,自己也没有做任何暧昧的遐想。
等涂完药他先行起身,那手指好似无意间从木棉的大褪上勾过,木棉浑身一颤,抬头时,涂抑明明浑不知情的在检查自己嘴角的伤势:“好像没那么痛了。”
木棉从桌上下来,收拾药箱:“你之前不是说打架不好吗?怎么这次就不忍了?”
“因为是为了学长,学长是不一样的。”
木棉拧药瓶的手差点失了准度,等他收拾好一切,脸上恢复了坚不可摧的冷淡。
两人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曾耀一行人也从医务室回来了,他脸上大大小小包了不少纱布,看起来十分惨烈。
秘书长对木棉使了个眼神,木棉借口让涂抑离开,两人进了办公室。
“副社,我问了刚才在活动室的成员,是涂抑无缘无故对曾耀动手的,把大家都吓得不轻,你看是今天开还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