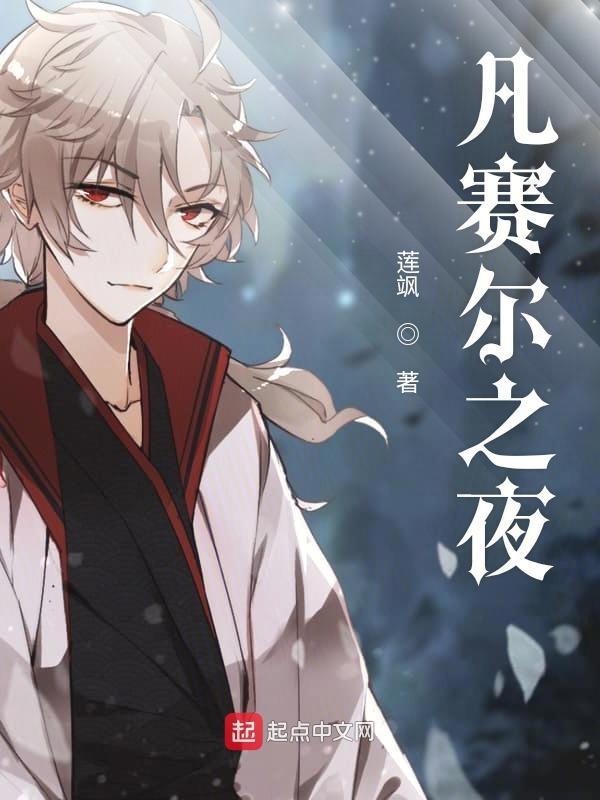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心机是什么生肖 > 第158章(第1页)
第158章(第1页)
他们联手设计了这一切。
“是他!父亲!是他们!是他们陷害我的!我并没有想——”
“涂啄,够了,很难看。”父亲的斥责从很高的地方直指他。
忽然,两句话在他的脑海里重现——
“父亲想要在国内扎稳脚跟就不可能和木家结仇,他尚且不敢怠慢木棉”涂抑在天台上说过的话,还有刚才父亲的不满——
“你怎么也来了?”
父亲是不明白这样的圈套吗?
当然不。
可一个不能得罪的大家族的独生子,只要他不在父亲眼前犯了错,父亲都可以选择包庇,就像就像父亲曾对他无数次的包容一样。
涂啄豁然明白了更多,木棉和左巴雅要做的不仅仅是让父亲亲眼撞见这一切,还要让他亲身体会左巴雅曾经的无奈——那种诉求无人搭理,眼睁睁看着涂拜包庇恶人的无奈和绝望。
“木棉”这一刻,涂啄再多说什么都是无用,他只能重复曾经败时的那种无助,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而是流了泪,“你好厉害呀。”
接着他点燃打火机,像个失魂落魄的伤心人一样将火苗丢向了地面,“轰”的一声,大火蔓延!
“学长!”涂抑瞬间把木棉护在怀里,然而木棉却一点惊慌的神色都没有,淡然地透过涂抑的肩膀,看那蹿腾的火光。
火光很快就起了侵吞一切之势,但管家反应很快,立刻冲佣人大声命令道:“你去拿走廊尽头的灭火器!剩下的人把楼下的灭火器也拿来!快!”
管家护在主人身前,涂拜自然也不会因这小场面而触动,他平静地拉着左巴雅后退几步,远离了燎原的火光。
很快,在管家的安排下众人熄灭了大火,在场无太大的损失,除了焚毁的房间门和地毯,还有离火势最近的涂啄一只手被烧伤了。
“哎呀,小少爷,赶快,拿药箱来!”
“不用麻烦了。”涂拜凛冽的声音透出一股无情的威压,“他要去的地方有够他治的。”
涂啄不愿相信涂拜的决定:“父亲”
然而,没有谁可以让涂拜心软,他稍显不奈地冲管家摆了摆手,继而牵着左巴雅走了。管家只好公事公办地对涂啄道:“小少爷,请。”
涂啄当晚就被送走,目的地自然是涂抑当年呆过的那个疗养院,在医生出具好转证明之前,他都不可能再回来。
庄园的这个夜晚哪里都不平静。
涂抑把木棉压在床上用力地折腾着。
“学长,原来你这些天就是在算计这个。”
木棉泡在汗水里爽快地笑。
现在无需他说,涂抑也明白了他费劲想弄清楚的一切。
涂拜对涂啄的喜欢当然不是因为他聪明,更不是他真以为涂啄拥有天真,相反,他无比清楚涂啄的本性,他清楚每一个流着坎贝尔血液的人。涂拜之前对涂啄的诸多包容来源于他那无师自通的完美伪装,他将坎贝尔家族的天赋运用到极致,所以深受涂拜的喜爱。自然,他对自己大儿子的不喜也是同一个原因,裸露的野蛮和残忍于他来说永远不被欣赏。
庄园的男主人疯狂而清醒,他不关心罪恶的尺度,只在乎脸上的假面。
那才是一个优雅家族世袭的荣耀。
正因如此,想要粉碎涂拜的喜爱也很容易,只要让他发现他钟爱的小儿子也有失控发狂的时候,也有可能在未来每一个贵族面前暴露他们家族的秘密。
与左巴雅会面之后被涂啄撞见是个彻底的意外,但很快木棉利用了那个意外。左巴雅不惜装疯暗示他,就是因为不敢让涂啄知道两人友好的关系,涂啄执拗地恨着每一个闯入他家中的人,一人纵能让他算计,两人便能使他发狂,发狂的疯子会做出什么,没有人敢赌,但木棉已经不得不赌。
酒庄那次便是个机会。
涂啄既已锁定目标,不如就看看他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
自然,他的疯狂超出了木棉的想象,当然也露出了诸多把柄——他暴露了自己的愚蠢。
没有什么比一个愚蠢的疯子更容易对付。
涂抑的表现加剧了涂啄的执拗,也消磨了他仅存的那点理智,既然他疯狂的巅峰是杀人,那木棉便给他杀。
只是天台之后涂抑定然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涂啄不可能再对他下手,所以他无法以自己为饵,便让左巴雅和涂抑在走廊演了那出戏,让涂啄的恨意很快转移到了左巴雅身上——
他最执着的家人离他远去的时候,他会彻底失去理智。
走廊的那一出成功刺激了涂啄,发了疯的蠢人想不到什么精妙的计划,他只会暴露自己最野蛮残忍的一面。
时间已经不多,他必须赶在婚礼之前动手。
左巴雅的装扮信号在这时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他深信穿着睡裙不做修饰的左巴雅意味着父亲绝不可能回到庄园,等到左巴雅精准地掌握涂拜行程之后,圈套开始上演。
针孔摄像头是提前就安装好的,这得益于涂拜的癖好,三楼是个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绝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涂拜回家的前十分钟,左巴雅给木棉发送了讯息。木棉通过监控画面确认涂啄开始动手后,便无需再留在花房,作为这计划最重要的一环,他必须也要成为撞破涂啄疯狂的其中一员。
没有什么比在外人面前暴露家族野蛮更能令涂拜愤怒,涂抑敏锐地察觉了木棉的计划,所以配合他,带着一众佣人和他一起上了楼。
如此,愤怒和羞耻加身的涂拜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已经很容易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