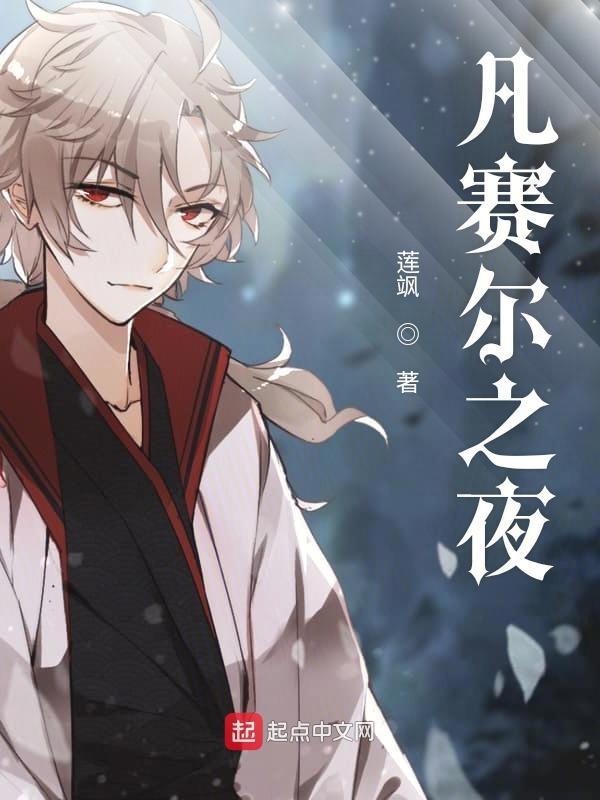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种子方面的知识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是回来了啊。”余歌边拿着破笤帚扫地,边说。
“后来呢?”邻居急切地问。
“走了啊。”
“走了?”他似乎有点不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干就走了?我还以为他们会强行把你赶出去呢,要不然就是跟你要钱……”
“您想到这么多,也没想到过来帮我一把?”余歌笑问道。
邻居吓了一跳,道:“我,我……你看看我,就是个糟老头子,瘦得排骨都能看见,怎么帮你呀?就算去了,也斗不过他们,你年轻,就是伤着了,也不难恢复,我要是受他们那铁拳一下,还不马上就死了!我乡下还有一大家子人呢……”
“我就是说说,您别当真!”余歌忙道,“昨天他们也没干什么,我打发他们走了。”
“就……真打发走了?”
“真的呀。”
邻居仔仔细细看了余歌几眼,“啧啧”两声道:“小余大夫,你可真有本事,我打以前看你,就觉着你不一般呢……”
“您可真是太过奖了。”余歌还记得,这位邻居,知道他与男人厮混,很是瞧不起,常和吴守愚打小报告来着。
“不是啊,我是想,你这房子大,就你一个人住,现在世道不好,恐怕不安全,不如你租出去,也是个收入,也有个人做伴儿不是?”邻居出主意道,“我最近遇到个人,想要租房子……”
“哦,那倒不用了,”余歌道,“我暂时还不想租呢,倒是打杂的,须得招一个,不然等医馆开门,那么多活计,我干不过来。”
邻居见余歌如此说,便只好笑了两声,道:“也是,小余大夫这么聪明,就算一个人,也能过得好得很,哪用我操心呢?”
一直微笑置之的余歌,竟变了脸色。
“是啊,”他说,“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果真是因为太聪明,所以不需要别人?还是因为太凉薄?为什么不想把空屋子租出去?是不是必须得承认,在内心深处,他还期盼着,有一个人会来?
第一次的露水情缘,以为日后不会再见,不料竟能重逢;之后历经两载,生死关头,又让他遇见了他,此后共度劫波,同历生死。现在,他们再次分别,还有没有下一次相见?
离开之前,余歌是彻底想清楚的:不管怎么样,他是走定了,纪崇基跟来,便和他一起生活;不来,就当是和他的又一场露水情缘。
终究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还是根本就是自己骗自己,以为他一定会来?余歌这一路上,的确是每天入睡前,都会想:也许明早他就追上来了?然而再睁眼,迎来的依旧是独自一人的一天。随着越来越接近潞州,这种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即使如此,余歌也依然会想:他认识这里,应该可以找得来的。‘
现在,也许是时候接纳这样一个现实,准备过一个人的日子了。同时,余歌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离开纪崇基的日子,真的已经变得不那么好过了。这一年来的日夜,怎能当做又一场露水来看待?现在想来,那一幕幕间——绯林外,将他双脚抱在怀里的山贼头领;七绝山下,挂着眼泪在他膝上入睡的谧南王之子;太平湖畔,为他挨了一刀,将他抱得喘不过气来的……情人——那时在他心中,所萌生的情深意笃,历历都是真的。而他亲手将之放走,又不愿自我怨恨,便只得不去想了。
“哪怕是路过,到这儿来看看,总是可以的,”余歌自己安慰自己,“总不至于一辈子都不见了。”
前堂的百子柜,余歌走前,是倒了一地,药品全倾的,就算不这样,放置过久的药物,也是不能用了。余歌写信给柏县百草堂,让他们运送些药草来,然后拿出针盒,到前堂开门迎客,暂且只作针灸,或是开了方,让病人别处抓药罢了。
第一天独自坐堂,病人寥寥,余歌写了招打杂的告示贴在门外,自认独居日子有了些起色。只是晚上做饭时,一不小心又做得多了,倒好像那个饭量了得的人还在似的。
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余歌估摸着,那帮地痞也该在思江水底摸到些什么了,跟百草堂定的药材还没送来,不过也应该是快了……来应聘打杂的倒有几个,可是全都不会认药,也没在医馆干过,余歌可不想从头教起,所以至今也没有招到人。告示被风吹破了,他又写了一个贴上,反正在药材运到之前,他还不忙。
这天来了个伤者,由人陪同着,来找余歌正骨。余歌摸了摸他的胳膊,皱眉道:“这是怎么伤的?可不好治呢。”
“被人打的!”伤者气愤地道,“现在外面,外有西夷人,内有山贼,哪儿都不太平呢!”
“山贼打断的?”余歌道,“这伤有阵子了,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才来?”
“我被他们掳去了,当然没法看大夫了!”伤者道,“差点儿送了我的命啊!要不是后来他们把我放了,我现在还不知在哪呢!”
“哎,对了,”旁边陪同的人问道,“他们抓了你,后来为什么又把你放了?”
“道走了一半,他们遇见了同伙,好像是他们的山头被什么……鸦山给占了,他们倒无家可归了!一伙山贼商量着要赶去报仇,嫌我们碍事,就把我和另外几个被掳去的人放了。”
陪同的人笑了两声,道:“也算是你命大,也亏得他们重义气,人家连他们的山头都能吞了,说明势力一定很大,他们却要去寻仇,真是以卵击石,想必没什么好下场。”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伤者道,“我就听见他们说,鸦山五个当家的,他们舍命,弄死一个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