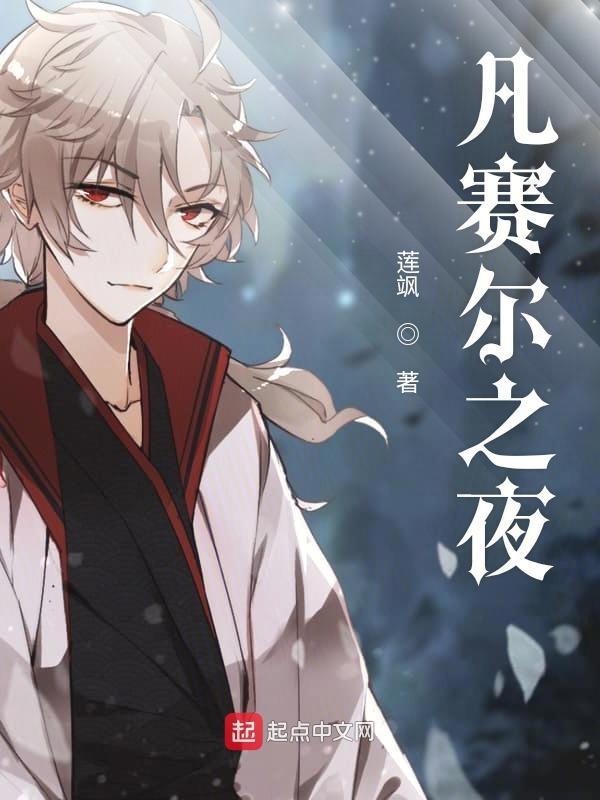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故人是指死人还是活人 > 第39章(第1页)
第39章(第1页)
无论怎麽说,好像就是从这件事往后,有人开始偷偷地传,说他床笫无能,好男风,且只好男风。所以究竟是谁来着?好吧,其实辛时到现在也拿不準究竟是谁,不过想想也是,这点拿不上台面的事哪里瞒得住宫中的耳目,怕是坐居明堂的两位圣人早当作笑话背地里讲过不知多少次,亏得他们没往外大肆宣传……
这样最好,辛时想。窥实他床帏间的癖好,神皇才放心让他在他们夫妻面前晃悠。不然他一届外男常与中宫国母私下对坐,流言蜚语不是没有,堂堂天子怎麽也不可能放任“奸夫”给自己带绿帽吧。
神后麽……辛时瞥一眼站侍中宫身侧的不知名女官,红腮黛眉,花钿珠簪,裙摆明豔华发宝气。连侍女都打扮得如此华美,神后的倾向已经很明显,她才不会对辛时另眼相看,只偏爱那种开朗张扬的。倒是神皇好像对他还有点兴趣,可能是听多他的私房乐子也想要身体力行尝试一把,看着他的眼神偶尔会带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也多亏神皇圣体抱恙,已有许多年不行房事,不然以中宫国母的手端,辛时很怀疑自己某天就会被药晕后送到大周天子的榻上。辛时自知容貌算不得多好,但阿真前曾经有个不怕死的侍僮,色欲迷心和他说,阿郎闷声轻吟,乖乖承接雨露的样子,别有一番滋味。
……唉。
他们夫妻两个,向来不在意这些。
辛时很肯定,如果时间再早个几年,神后一定会那样做。神皇好美色,这件事是拦不住的,与其防不胜防地让他倒腾几个孩子出来,还不如就找点男孩玩玩。
神皇啊……辛时的思绪稍微飘忽开一点,便觉得有些寒毛倒竖。即便那是大周的开国天子,也还是算了吧。白日对诏拟旨已经够忙,他可一点也不想晚上再折腾,整日整夜都没得觉睡。
又不能当皇后。
说起来,神皇那唯一庶出的儿子也该有八岁了,却像是不存在一般,从没听说过消息。他的生母,是叫张夫人吗?犹记得是北海亲征时带回来的,仗没打赢,却是搞大了女人的肚子,也难怪神后看得紧,果然是一不留神就得惹事……
“一面看一刻钟,有那麽好看?你要是病还没好,就趁早滚回家歇着,别来我面前撒癔症。”
神后语气微冷,显然对他的走神很不满意,辛时急忙谢罪。
神后又问:“看出什麽来了?”
辛时支吾一声,急忙去扫奏上的内容。还好,不是什麽繁杂的文书,看字体还有些熟悉,好像是阿韵写的?
辛时草草瞥几眼,悉知大致内容,立刻道:“臣以为……很好。莲目僧合药可解陛下病痛,若依其言供奉,定能保圣体长安。”
“是挺好,只是陛下如今越发依赖僧道了。”神后叹息。“可又有什麽办法呢。这病痛,治又治不好,只能求神拜佛地寻些慰藉。”
辛时又道:“今次初春陛下为大佛开光回驾,此时也像是了却因缘。”
神后便看辛时一眼,忍不住笑一声道:“呵,你倒也懂佛理了,那莲目僧在陛下面前,也是同样的说辞。他至神都四年,我还以为是为求名亦或利,如今看来,真有些高僧样态。”
辛时默默放下奏折,心照不宣地与神后谁也没提天子今年初春从骊山回转太早以至染病,究竟是为了礼拜神佛,还是指点太子国事。但这位莲目僧——辛时知道,就是向二圣进献释迦佛骨以至兴修云法寺的那位,上回去采风的时候还没见着来着,说是闭关清修——如今看来,消息也很灵通嘛。
神后道:“那一百卷经文,我已命人抄去,约后日交付,镶成卷轴,我又另加八卷,下个朔日一并送入寺,这些由阿吴负责。在此之前,你将所有卷文全部校检一遍,保证无惫懒残篇缺页之类,懂了没有?”
辛时立刻头疼了半边,却依旧神态谦逊道:“此事当为臣之分内。”
神后微一颔首,略显满意。
“前几日你不在,该办的文书,都叫阿韵写了。”她又道。“她太久未曾操笔,却是手生,紧急的已经发出去,其余还留按着,你回去看一看,替她润色一番。”
将日常该议的事议完,辛时从长极殿中告退离开。
春阳明媚,送来的风里即便还有寒气,也不再逼人。道两旁的树木娇娇地冒出嫩叶,辛时盯着半绽的花蕾看,不知第几次在心里给自己打警钟——与神后议事的时候,不要走神。
嗯,他最近和杨修元相认,蜜里调油在家黏乎几日,有点得意忘形了。
得意忘形的年轻翰林回到属院,薅一把树上叶子,唉声叹气。今日是十二,离下个朔日还有十八天,经卷交付还需两天,整卷也需要二至三天,装轴没个十来天做不完,留给他的只有三天。一百卷长经,三天校完——杀了他算了。
在矮几上趴不到半刻钟,辛时又坐起来,抖擞精神。没关系,再忙也要等其他人将抄好的经纸整理完,辛时找阿韵对完旨中圣意,文思泉涌地按着文中思路修改,待到刻漏一下申时,立刻毫无留恋地从座上站起,收拾东西,摘牌,取马,归家。
骏马飞奔在神道上,尘土飞扬。掠过某处沿街高挑的角楼时,楼中舞姬舞地正欢,长袖一甩铺开,仿佛可摘星辰似得,暗绣金线的水红缎面熠熠生辉,与热烈的歌声一起,从头顶扑面而来。
“劝君莫惜金缕衣,
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