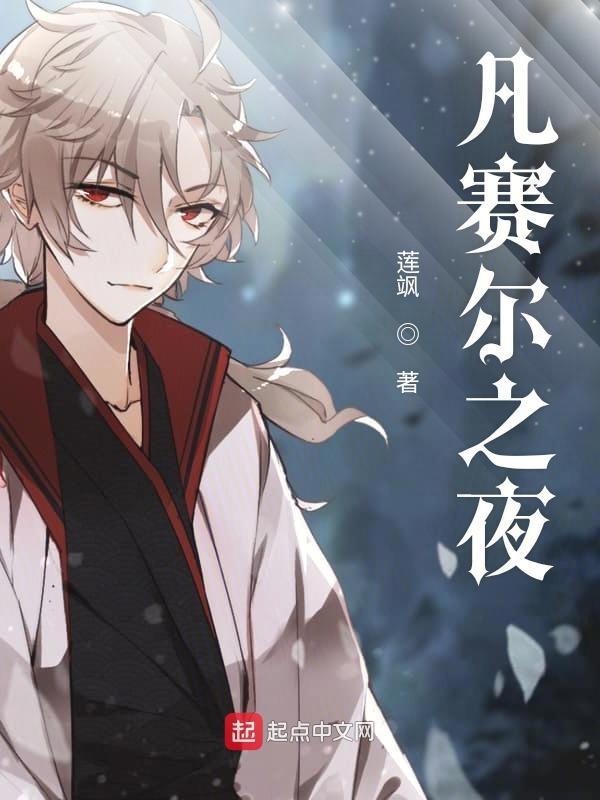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花信风什么意思 > 第216章(第1页)
第216章(第1页)
在大会上发言游刃有余的人,一时间竟然也语无伦次了。
且惠啊的一下,“关主任怎么听的?我明明说的是去京大,他怎么乱说。”
“不要紧,不是真的就好。”沈宗良闭上眼,两只手把她揉到了怀里。他以为他又要失去他珠玉光辉的小姑娘。
且惠在他肩膀上点头:“是啊,我本来准备昨晚跟你说,下车的时候又忘了。”
沈宗良一迭声地说没事。不是要一走了之的话,好像怎么不尊重他都可以,他也不会在这份小节上计较。
且惠推开他一点,隔着夏末的一点日光看这个男人,指尖刮了刮他的鬓角,心里像不防备抿下了一口醋,热热地酸胀起来。
她又说了句对不起,“你好担心我走掉,对不对?”
沈宗良偏了下头,眉头皱了又皱,才终于承认:“对。”
且惠看着他,他也看着且惠,话说完了,谁都不愿意出声,时间在静默里流淌过去,没多久,两个人不管不顾地吻在一起,当事者也分不出究竟谁更急切。
沈宗良细细密密地吻遍她的脸,他薄薄的嘴唇像一把小刷子,且惠闭起眼睛,只剩张着嘴大口呼吸的份。
好空,上面和下面一样空,空得她想放声叫出来。等他吻过了鼻尖,一感受到那份滚烫的气息,且惠就往上挪了挪,找到他的唇,一张一合地含着他吻。
沈宗良把她抱起来,走到更里间的休息室,把她压到他平时午睡的床上,湿热的吻从耳廓后印过来,又重又急。
他咬她小巧的耳垂,声音哑得像病了一场,“说你爱我,说你不会离开我,小惠。”
且惠颤栗着,毫无章法地摸他的脸,一只手去解他的扣子,“我舍不得你,我爱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们会结婚,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这几句话简直比催情药还厉害。
沈宗良重重地chuan起来,不住吻着她的脸,“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你陪着我,我也陪着你。”
好一会儿了,且惠一双手扒着床沿,无力地跌下来,眼神涣散地看洗手间。
为非作歹的人恋恋不舍地从后面贴上来,“你走不过去的,我抱你。”
“嗯。”她点点头,“别让人进来就行。”
且惠清洗完了,把刚才被卷到腰间的裙子放下来,好在没多少折痕。
她对着镜子照了照,一点红晕从她的耳尖蔓延到锁骨上,和眼尾的绯红如出一辙,是个明白人就能看出来,自己刚经历了一场怎样激烈的情事。
沈宗良坐在外面沙发上,一支烟还没点上,她就匆匆走了出来,说先下去。他叫住她:“不准去,坐这里休息一下。”
腿抖成那个样子了,还要打着小跑去办公室,摔上一跤不得了。
且惠撅着嘴瞪他,“都是你那么用力。”
沈宗良抬眼看了她一眼,懒得和小孩子争这种意气,也不知道刚才谁一直胡叫着“daddy”、“老公”。
他拿烟指了下沙发,“就到这儿坐,这会儿没人上来。”
“看见也不要紧了。”且惠大起胆子坐下,“我都不在华江了,还管这些呢。”
沈宗良温柔地笑了下,拉过她的手,故意说:“哦,你是走了,对我有影响你也不管了?”
且惠哼的一下,“我都管不过来自己的事了,你还要我来管吗?”
“你什么事?”沈宗良拉着她坐近了一点,听见她烦心就不大适意,皱着眉问。
这么笔挺地坐着太累,她干脆贴到了他身上,“年底就面试了,紧张呀,我得抓紧时间复习专业了。也不知道我那份攻博计划写得好不好,教授会打多少分?”
沈宗良还以为是什么。
他笑了下:“那就先给老高过过目嘛,这也能叫事?”
且惠疑惑地嗯了一声,“老高?”
“高跃民是不是?法学院的院长。”沈宗良抱着她,回忆起在美国读研的时候,“他那会儿在斯坦福进修,我和他做了一年邻居,一馋就来我这儿蹭中餐吃,报销了我多少好酒!”
瞠目结舌过后,她阻止了他追忆往昔。
且惠说:“停,不要再说了。让我对老师有点幻想。”
沈宗良看她摇头晃脑的就想笑。
他点了下她的额头,“早就教过你了,不要把任何事物看得太完美,这有什么?老高也不是神仙,总逃不过一个油盐酱醋,但这妨碍他在学术上受尊崇吗?不妨碍的。”
且惠几根手指互相掐了掐。她低头说:“就知道教训我,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要去北边读博呀?”
“好,我来问。”沈宗良配合她说:“为什么要去读博?”
且惠得意地说:“原因当然很多了,我之前读研的时候浑浑噩噩,总想再念几年书提升一下,加上自身的性格、喜好,将来的发展,还有集团合规上的亲属任职回避制度”
沈宗良听到这里,他说:“你等会儿,你在华江还有其他亲戚吗?要避谁?”
她她说的当然是结婚以后了!
且惠看他一脸问号,气得在他大腿上拧了下,“我、我不和你讲了,我要回去。”
但沈宗良把她抱得很紧,她挣不动。
他摩挲着她的手背,说:“好了,考虑这个没必要,我也不会在华江待很长时间,就算是我的太太,还是可以继续留任,这没关系。”
他说我的太太的时候,语气是那么笃定、温柔,让且惠的心跳停了一拍。她红了脸,“有谁说要当你的太太吗?我可没有哦。”
说到这里,且惠推开他起身,脚步匆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