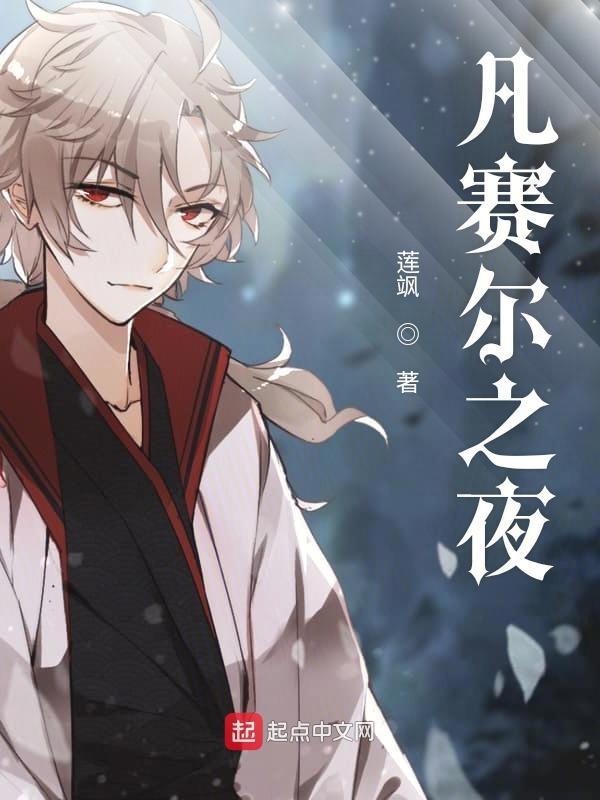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女名医成长手册于星火 > 第4章(第1页)
第4章(第1页)
张升照现在在公立的县学里读书。北宋设了公立的乡学、县学、州学,不收学费,但是每日要收取伙食费。
张秀才正要出门,心不在焉地敷衍儿子:“知道了,改日再说吧。我今天有事,再不出门就迟了。”
他今天穿上了自己唯一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衣衫,打扮一番,看起来满脸红光,格外体面。
出门前,张秀才对正在洗衣服的马娘子说:“秀姑啊,你有空就给孩子整点饭食,带去书院吃。那书院里的日食费又贵,弄的饭还没家里的好吃。”
马秀姑抬起头,手还搭在盆里,应承道:“好。官人要出去吗?”
“我约了人。今晚不用备我的饭。”
家里早就没有钱了,却不能阻止张秀才出门喝酒的脚步。
剩下的米面也不多,没钱没粮不好过冬,孩子读书的饭食更是无从着手。
马秀姑在心里叹气。
怎么办,怎么办呢?
可这些话就算说了,她这个官人也只会答非所问,说些车轱辘话应付她,和他说还不如自己想办法。
她便只道了一句:“入冬了夜里冷,官人早些回来。”
“知道了。”
张伏林有点不耐烦,没多看妻儿一眼,就连儿子站在身后眼巴巴的看着他,他也没在意,匆匆就走了。边t上的张升照失落地低下头,马秀姑看着他,欲言又止。
这个年纪的男孩子自尊心很强。一起读书的同学们都在县学吃午餐,他只能吃家里带去的冷干粮,同学会看不起他。
这时,有人从外面走进来,带着偏低沉浑厚的嗓音边走边说:“大嫂,这冷天,你就用热水洗衣服吧,别心疼炭火。”
张善云认得她,是住在隔壁的二婶婶,高淑英。
隔壁家的二叔张伏松也是张善云最讨厌的那种男人,嘴巴坏,不学无术,吃软饭。但二婶却是个极好的人,明辨是非,又非常心软,时常接济她们家。
“大哥又出去和他那些同年喝酒了?”高淑英蹲下来,伸手就去接马秀姑盆里的衣服洗。“手里就那么点钱,有什么好聚的。聚了那么多次,也没见谁来提携提携他。”
马秀姑连忙道:“淑英你别洗,我这马上就洗好了。”
她把弟媳妇手里的衣服抢过来,拉着弟媳起身,好声好气地说:“官人说了,他们同年考上的秀才,多聚聚交谊就深厚起来。他日仕途相遇,还可以相互照顾。”
高淑英嗤笑一声。“想的真美。”
她把手在衣服上擦干,从衣襟里摸出一个小袋,塞到马秀姑手里,语气不满道:“别人升迁了,难道还会因为跟他吃了几顿酒的交情,到时候为他请托一把?家里的事他也不管,几个儿女也不知道看顾。”
高淑英说着,越发有些生气,“他以为他这种人能娶到这么好的续弦娘子容易吗?人家要么是嫌弃带着他两个孩子,要么是嫌弃他三十多岁了还只是个秀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收入微薄养不起家。也就嫂子你,肯嫁他这么个人。好不容易又成了亲,他也不知道收心,照看一下家里。”
马秀姑被逗笑了,回道:“我这样的相貌,能找着人家就不错了。”
她打开手上的布袋子,发现里头是五两碎银。
弟媳竟然给了她这么多钱,怎么使得?
她连忙把袋子还给弟媳。“淑英,你这是干什么?快拿回去。”
张善云知道现在是北宋仁宗时代,根据她“出生”以来这几年的观察,再根据大米价格换算,这时期的一两银大约折合人民币八百到一千块钱。婶婶给的五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五千块的大红包,够他们一家人吃用近三个月。
马秀姑手里的钱袋子到底还是没能还回去。
高淑英缩回手举到半高,马秀姑塞了个空。她高举手在面前搓着,哈着热气说:“你拿着吧大嫂。快过年了,给孩子们买点好菜吃。照哥儿书院里的食费,也得去结了,哪家哥儿读书是要从家里带饭食的?”
她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张升照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张善云看向她娘亲,果然看到马秀姑面上迟疑不决,又带着愧色。
高淑英说了一句:“医馆夜里还要守门,我先回了啊。”
她走到门边,拍了拍站在门口的张升照的肩膀,温声说:“照哥儿,等会儿去巷子口买些肉菜回来,叫你娘别亏待了妹妹。”
十五岁的男孩子,个子已经很高,又瘦,完全是一副倔强的少年的模样。
他也觉得羞愧。
父亲这样不好,老是要叔叔婶婶接济。
不过,等他以后考中了举人、考上了进士就好了,到时候再还给叔叔家。
最终还是没说别的,他只低声道了一句:“婶婶慢走。”
张善云被惠云拉到母亲身边,又被安置在小椅子上坐下。
二姐惠云拿起盆里的衣服,一边绞干水一边说:“娘,您去里屋歇着,衣服我来晾,一会儿我来做饭。”
张升照走过来,一声不吭的也帮着绞衣服。
张善云随即也站起来帮忙,从哥哥那里递衣服给姐姐晾。
马秀姑把手往衣服上揩揩干,说道:“娘不累。”
她面上带着笑容,“等开了春,要让惠娘和善娘也读书认字,学算术。”
这件事她考虑了有一段时间,本来打算趁过年时候去做帮工,攒够了钱再和两个孩子说,现在有钱了,索性说出来让孩子高兴高兴。
“东街的陆员外家请了一位老学究,在家给姑娘们上课。高婶婶想让娇姐儿也去听,陆家的夫人已经答应了,说只要给学究送束脩就行,不另外收钱。现在有了这些钱,咱们家的束脩也不用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