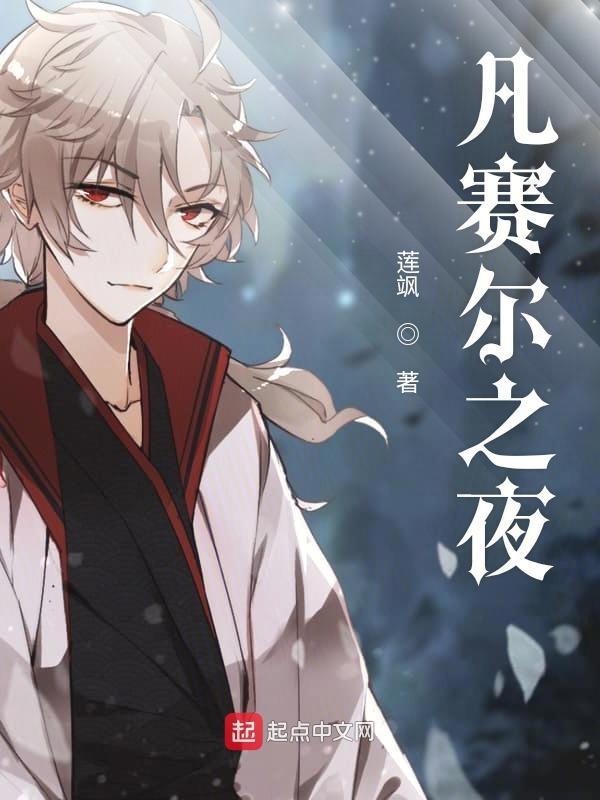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青天在上任人狂 > 11 章(第2页)
11 章(第2页)
我看向梁熠。
阳光从窗帘罅隙里透出斑斓的光影,稍稍照清他的轮廓。
他的鬓角连向下颌,是一道好看流畅的曲线。
而此刻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手指攥紧我的被角,看上去,他十分在意我的回答。
或许,我该抓住这次机会。
于是我垂下眼帘,声音低低:「你问我为什么替你挡子弹,你还不明白吗?」
他声音发涩:「明白什么?」
我看向他,眼眶沁出泪来,声音都带着哭腔,「父母死后的这十年,我看尽人情冷暖。从前与我父亲称兄道弟的那些人,像赶一条狗一样赶走我。把我捧为座上宾的梨园师父,得知我家破败后翻脸就不认人。但只有你,费尽心思想把我留在你的身边。你没有明说,但我知道,如果不是你,我哪能活得这样洒脱快意。阿熠,这世上真心待我的人,只剩下你了,我宁愿,宁愿替你死。」
你看,唱戏最要紧的是代入。
我的表白是假话,但从前的辛酸却真得不能再真。
正因为这一份真情实感的辛酸,我忍不住嚎啕了起来。
就好像,我果然爱慕他至深,并为这一份真爱伤心不止似的。
梁熠怔住,猛然抱住我。
我埋首在他颈侧,两臂抱紧他不肯放,由着眼泪肆无忌惮地掉进他的衣领,「阿熠,阿熠,我们不要吵了,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梁熠紧紧抱着我,心跳一声快过一声。
他没有说话,拇指轻轻揩去我颊上泪珠。
良久,他叹息一声,捧着我脸庞,在我额上印下一个吻。
极温柔,极缱绻,仿佛重幕筛过的寸寸日光,许诺要将万物照亮。
17
我用一次重伤,换来了梁熠难得的心软。
他喜欢从前娇气天真的云卿,我就顺势扮给他看。
赏花品茶、读书写字,都是从前的云卿会干的事情。
十七岁家变,我再不碰这些烧钱的玩意儿,转而去学如何调笑,去学如何斟酒极满而不漏一滴。
欢场十年,我学会了假装。
初出茅庐时是假装成熟老道,而现在,我是要装温柔真爱。
我去裁缝店新做了五套不同款式的白裙,又一口气买了十七盆鲜花。
书店里新进的西洋油画,我买了大大小小的八幅,甚至在梁熠书房的国境地图边也挂了一幅。
我常常抱着梁熠的脖子撒娇,跟他谈天谈地,又在他不耐烦的时候装委屈说无聊。
终于,梁熠答应我可以继续我的京剧事业。
只一条,不许涉足欢场。如要赴宴,必须是与他同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