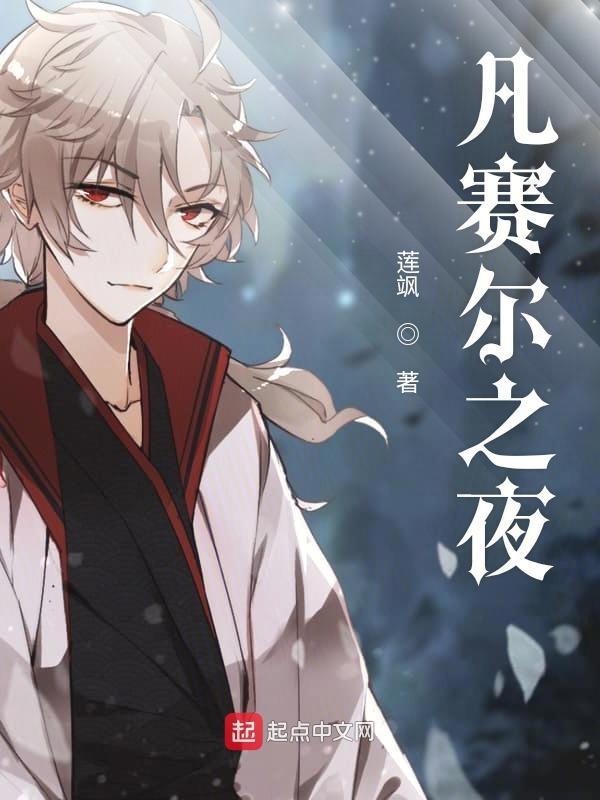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被秦始皇赐婚扶苏之后作者kono昭财喵 > 第 97 章 成为3s任务者的原因(第1页)
第 97 章 成为3s任务者的原因(第1页)
宴会前,似乎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少年突然想起了这件毫不相关的事情。
来势汹汹的阴云将人笼罩其下,一整个天幕,都被黑暗笼罩得透不进一丝光线。
雷电将天空劈成两半,如同一道巨大而可怖的深渊,丑陋的横陈于天际。
“轰隆”的一声巨响,跟扶苏听到惊天噩耗时的感受毫无差别,狂烈地快要将他整个人撕得粉碎,吞噬得什么都不剩。
痛苦、惊愕、仇恨,这些情绪会给人带来什么?
扶苏头重脚轻。
他人似乎还是那个人,表皮下的血肉却已然重组,在刀剑相加,斧凿所劈,伤口与疤痕层层叠叠的累计下,重新汇聚到一起。
但这样的痛苦的组合物,真的仍然能够被称之为原先的他吗?
这一点,就连扶苏自己都不知道。
少年目光沉沉,再次扫了眼室内。
门口、床榻、窗台。
这些都是他和她相处、纠缠过的地方。
若是放在以前,他会时常来到这些带有甜蜜记忆的地方停驻,一遍遍的回味那段美好的时光。
但现在,就连他们俩一起呆过的地方,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罪恶,而那些“甘甜”的回忆,更是竖在心上的倒钩尖刺一样,每每回翻看、拨动,都要将他撕扯得血肉模糊,遍体鳞伤。
扶苏并不拒绝这心如刀绞的痛楚。
作为罪人,他合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骨节分明的手指伸出,少年一寸寸地抚过那人曾躺过的床榻,上头,还残留着浅淡的温度,又像是他的心,一点点从滚烫变得冰冷。
“太、太子殿下,”
门外的人仓惶而惊恐,从扶苏不断陷入沉默的反应中嗅出了风雨欲来的不平静。
他明明亲眼看着那人闯入屋内。
殿下却三番五次地为其遮掩,直到如今,还要强调自己对刺客的去向一无所知····
这难道不能说明,太子与刺客本就是一伙的吗?
“杀身之祸”四个大字出现脑海。
他面色霎时间变得苍白,满心都是今日不该来这一趟的悔意。
“殿下,属下还有些事,就此告——”
轻轻闭了闭眼,少年再度睁开时,强压下了眼中的伤悲。
少女已经离去,屋外之人却还没有。
能一句接一句的将他逼问到这个程度,必然是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终究是···留不得啊。
扶苏面容冷硬地走到墙边。
上头,挂着一把开了封的,寒光凛凛的宝剑。
并非青铜,而是能够映照出少年脸庞的玄铁利剑。
取到手中,掂了掂与青铜剑毫不相同的重量,扶苏垂着眼,泄出一丝杀意:“隔着道门,孤听不大清楚,阁下还是进来讲吧。”
又是一道惊雷劈过,雨声
渐起。
昏暗的厢房内,一个中年人双目睁大,嘴巴诧异地张开,脸上是惊讶与疼痛混合后的难以置信。
那本该是张灵动的面容,但现在,他的神情凝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动作也保持着想要从房间里逃出去的姿势。
血液从剑尖滑落,扶苏抿着唇,半张脸浸在阴翳中。
最后一次,这真的是他最后一次帮她。
黎筝很忙,忙着处理刺杀的事后收尾。
泼到魏国公子魏豹身上的脏水要泼严实,自己差点被抓所泄露的“女刺客”的消息要死死压下,回身还有“粮票”的正式推行等等等等一应事务要处理。
黎筝忙得脚后跟不着地,已经有大半个月没有再见过扶苏了。
或者说,她不敢见扶苏。
巫女白马甲不敢,赵黎的马甲也不敢。
她一股脑儿的在嬴政那里接下了一大堆活计,只为将所有的空余时间全都填满,让自己没有任何闲工夫胡思乱想。
“真的只是担心自己会胡思乱想?”
装作爬山虎,覆盖了黎筝身边小半片墙壁的121冷不伶仃地发问。
黎筝身上压着的活根本不止前头所提的那些,还有棉花的试种推广、魏楚两国对昌平君之死所表现的态度,以及刺杀那日精兵队伍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