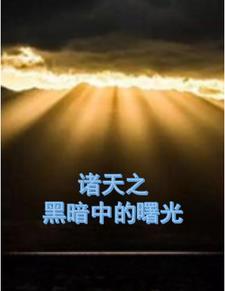格党党>怎敌他百般引诱_雪夜戏猫 > 第86章(第1页)
第86章(第1页)
那人还未说话,一旁静坐许久的老妇人忽地站起身,颤巍巍地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巴掌,恨声道:
“你这个混账东西!快放阿茹离开罢!你老子娘忙乎了大半辈子给你娶了这么个媳妇,你却天天赌博吃酒,每每喝醉就打老婆!如今还逼着一家人给你一道演戏,想讹人家的钱!我这是做了甚么孽哟,生下你这么个混账……”
她絮叨咒骂着,气得身子直颤,众人听到了她所说的话,终于捋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呸,这么大个汉子,好赌成性殴打妻子,买了假胭脂给妻子用,出了问题后带着一家人来演戏讹人来了?真是不知羞耻!”
“你快说,你的假胭脂是哪里来的?画浓斋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可不能让这样的假冒伪劣坏了名声!”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伐着他,那大汉扛不住,连忙答应了颜荔的要求。
“姑娘抬抬手儿放过我吧,这胭脂是我在城东香茶巷一个溜街串巷的小贩儿手上买的,他竹筐里放了许多,因价格低廉,有许多人买呢。”
颜荔若有所思,命人写了封放妻书过来,让他签字画押,名唤阿茹的妇人也签了。
自此,两人再无瓜葛。
看热闹的人渐渐散了,老妇人也被小儿子搀扶着离开了,临行前,她两眼含泪,看着前儿媳,“阿茹,以前都是婆婆没用,让你受苦了。”
阿茹亦红了眼圈儿,摇了摇头,“婆婆待我很好,都是他的错罢了。”
两人依依惜别后,颜荔见艳阳高照,已近日午,便道:“忙了一上午,想必大家都饿了,今日我做东,请大伙儿去醉仙楼吃顿好吃的。”
于是便临时关了铺子,一行人直奔醉仙楼而去。
青睐
颜芙与霍长川在京城又住了几日,便动身前往庆州。
临行前,霍老夫人吩咐人装了许许多多补药,叮嘱道:“这都是些上好的药材,最是强身健体的,煮茶煮粥饮也无大碍。”
霍长川有些无奈:“娘,我的身体不是好好儿的,没必要补。”
“那怎么一样!如今你是成了家的人,自然与以前单身汉时不同……”
见她老人家似乎还要说些甚么不得体的话,霍长川连忙打断:“好了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此时已是七月底,天气仍十分炎热,盛夏阳光下,三辆马车缓缓驶离京城。
颜荔送走了姐姐,心里空落落的,与文若兰坐在铺子后的小院儿里乘凉。
吃了颗冰湃葡萄,她望着窗扉下的芭蕉叶出神。
文若兰小口饮着酸梅汤,目光也有些游离,似是有甚么心事。
夏日炎炎,蝉鸣阵阵,阴凉桐树下,两人躺在藤椅上皆有些困倦,就在昏昏欲睡之际,门帘子忽地响了一声,孙大娘洪亮的声音传来。
“姑娘,香茶巷那边有结果了。”
颜荔登时精神一振,忙问:“怎么说,可找到那小贩儿了?他可说出了背后供货之人?”
孙大娘道:“招旺在巷子里整转了两三日,终于又遇见了那个小贩儿,他果然挑着竹筐,走街串巷地吆喝。”
她拭了拭汗,继续道:“招旺这孩子机灵,知道不能打草惊蛇,便过去套话,佯装要采买许多胭脂,要跟小贩儿回家去取,可他十分戒备,只让招旺明日再来,他准备好他要的数量给他。”
“招旺虽走了,招财却悄悄跟着那人回了家,见他放下竹筐关门略作歇息,便戴着小帽儿出了门。”
“紧随其后,姑娘您猜怎么着?那小贩儿竟来到了一座铺子的后门,鬼鬼祟祟地进去了。”
颜荔问:“甚么铺子?”
孙大娘鄙夷地哼了一声,道:“就是东街那家‘晚霞斋’!原来是他家搞的鬼!月初开业,生意不怎么红火,没想到老板竟然这么黑心,自己的东西不好,便想着做假货来卖,污蔑抹黑旁人!真真是不要脸!”
颜荔想了想,道:“捉贼捉赃,咱们得想个法子捉个现行才是。”
文若兰挠了挠头,“这……应该怎么做?”
孙大娘道:“不如让招财去作证人,指证他们家作假?”
颜荔摇了摇头:“不妥,万一走漏了风声,让他们提前做了准备,再想抓住甚么把柄可就难了。”
三人相对而坐,想了半晌,皆没甚么头绪。
孙大娘一拍桌子,抬高声量:“不如直接将人抓到衙门去,严刑逼供,由不得他不说!”
颜荔不禁笑了:“这怎么行,如此一来,咱们这被偷盗污蔑的人,岂不成了恐吓他人的坏人?”
“那可就难办了。”孙大娘叹了口气,“但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时日久了,可是要坏了铺子的招牌的。”
“管是一定要管,就看如何做了。”
又想了一会子,着实没甚么好法子,孙大娘去了铺子里与阿茹接待客人,颜荔便与文若兰在藤椅上小憩。
到了太阳下山,热气渐渐退去,颜荔才觉得浑身恢复了几分力气,正想着要不要去翰林院找应策,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
“姑娘,云太妃派人前来,请姑娘过府一叙。”
颜荔愣了一下,忙道:“稍等片刻,我马上就来。”
后院有两间厢房用来歇息,颜荔常来铺子里,房中便放了些她的衣物用品,她匆匆换了身衣裳重新施妆,跟着七王府的人去了。
自打上次她在街上偶然间帮云太妃解了围,她老人家翌日送来许多贵重礼物不说,还隔三差五地便邀颜荔过府游玩。
云太妃似乎十分喜欢她,不止一次地提及要认颜荔为义女,都被颜荔佯作惶恐地给婉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