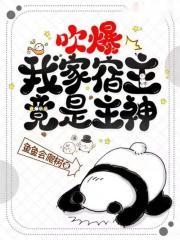格党党>念念有词的意思 > 第10章(第2页)
第10章(第2页)
这座城市很大,即便是这个时间也还是十分流光溢彩,贺忱觉得自己身处其间,是很小很小的一粒微尘。
路程不长,陆一昼很快就把贺忱送到了,车停在贺忱家楼下没熄火,贺忱推了下门,没推动,便转头去看陆一昼。
陆一昼这才开了车门。
“那我走了。”贺忱说。
雨还没停,陆一昼道:“后备箱里有伞。”
“没关系,就几步路。”贺忱说。
他走进单元楼的时候有一点想回头,但还是克制住了。
他租的这栋楼是老破小,没有电梯,需要走好长的楼梯上去,在往上走的过程中,贺忱的脑海中浮现出陆一昼在“晚钟”门口帮他打人的样子。
暗淡的雨夜,陆一昼高挺的身形,说话时的声音,身上清淡的气味。
贺忱的睫毛颤了颤。
然后他告诫自己,不要再想下去。
他们两个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云泥之别,他不能再对陆一昼生出不该有的想法。
方才拒绝陆一昼的伞,也是怕后面还要再还,还要再见对方。
陆一昼在贺忱家楼下停了很久才走。
他从车窗里往上看,直到有一个房间的灯亮起来。
他很轻易地推断出了贺忱住哪一层,门牌号是多少。
就算什么都看不到,但他还是好像能想象到贺忱回家之后都做了什么,进门换衣服,坐下喝水,之后去洗澡。
陆一昼的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他的手按上贺忱留在副驾驶上的毛巾,有一点用力,昂贵的毛巾被他攥出了褶皱。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走,一开始没放贺忱下车,是以为对方会邀请他上楼。
陆一昼又回忆起在酒吧门口看到贺忱的样子。
对方没打伞,冒雨跑到便利店去买折价饭团,衣服都被淋湿了,像只没有家的小动物一样。
他也形容不出自己当时的感受,但心脏确实狠狠地跳了一下。
贺忱当年甩他甩得那么绝情,他却还是没办法在别人欺负贺忱的时候视而不见。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陆一昼也说不清。
他只是觉得自己不长记性,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闭上眼睛,还想得起贺忱大学时的样子。
谈了两年的恋爱,贺忱在毕业的时候告诉他要分手,没有理由,态度坚决,不存在任何转圜的余地。
他以为贺忱一定按照那时候的规划,进了全国最好的舞团,却没想到会在一次商务宴请结束后的酒吧聚会上看到他。
贺忱那天穿了件很露的衣服,跳舞的样子也是他没见过的。
陆一昼不清楚贺忱为什么会在那里,但他非常、非常失望。
他以为贺忱比谁都把梦想看得重要,没想到对方会有一天变成这样。
是缺钱吗,为什么不告诉他,不来找他。
陆一昼不知道贺忱的生活中都发生了哪些事,这让他觉得不太舒服,而贺忱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淡,就像两个人之间没来没有过那么亲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