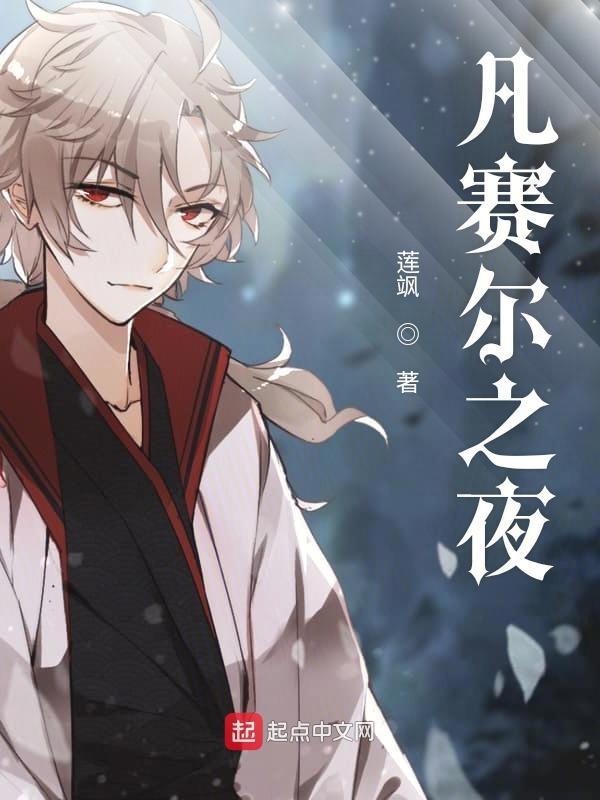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逐王的攻受是谁 > 第91章(第1页)
第91章(第1页)
“放我走吧……”
“你说什么?”听他要走,陈霂更觉心痛难当,“不行,除了这个,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我会尽我能给的一切对你好,但我不会放你走。”
“让我带季槐离开晟京,我不能再留在这里。”
陈霂急了:“你为何这样在乎那个女人?你又不爱她!”
元南聿沉声道:“她是张榕将军的幼妹,我曾起誓,今生要善待于她。男子生于世间,不求高官厚禄,显亲扬名,最起码不能带累亲眷,让妻儿因自己受苦,我却连这些都没有做到。”
元南聿在北境本已官至右都督,却因对自己有情,背弃了封野和燕思空,已然失了忠义名节,若连妻儿也不能保全,更会让他羞愧难当,无颜立足于天地之间。
这一切因果,竟全都是因为自己。
陈霂思及此事,不免心中酸涩。
他惭愧不已,对元南聿耐心哄道:“你且放心,你挂心之事,我自会想办法替你解决。”
“你又要做什么?”
元南聿如此警觉,陈霂心痛之余却只能恼恨自己:“你不必多想,我既知你对我有情,又从无背叛过我,我便不会再做让你伤心之事。”
“陈霂,你说不会再伤我已不是一次两次,如今你让我如何再能信你?”
“你不用听我今日之言,只看我究竟能否做到罢。”
————
陈霂忧心元南聿身体未愈,又怕将他强留身边惹他厌烦,就派人护送他至北苑行宫修养数日。
元南聿因季槐不肯体谅自己,又生了怨怼之心,想暂时不与她相见也好,便顺了陈霂的意思。
有诗云,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元南聿掐指细算,他此次来京,竟已有一年之久。
这一年里,他几乎没有一日身心是放松的,既是存了对封野燕思空的歉疚之心,又时刻担心季槐会被自己连累,惹来陈霂责难。
家国亲眷,都系在他一人心里,怎不叫人疲惫?
陈霂这几日并未现身,元南聿索性什么也不想,将一颗心稳稳地放到肚子里,他这些日子身体透支的厉害,现在松懈下来,才感觉到了疲累。
元南聿心道:到底是年岁渐长,越来越受不住打击折磨,不知这从容看云卷云舒,闲庭落花的清幽岁月,还能有几时?索性就依着自己心思,在这皇家行宫纵情享受一番,才不算辜负。
他突然想起了,曾与陈霂一起去过的那处温泉。
那小池附近环境清幽,现在天也凉了,自己从戎多年,又曾受过重伤,身上旧疾这几日隐隐发作,各处关节酸痛的厉害,不如过去泡泡,兴许能让身上好受些。
用过晚饭,元南聿只身去了温泉处。
出了暖阁,到了池边,见四下无人,元南聿索性将身上浴袍除净,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