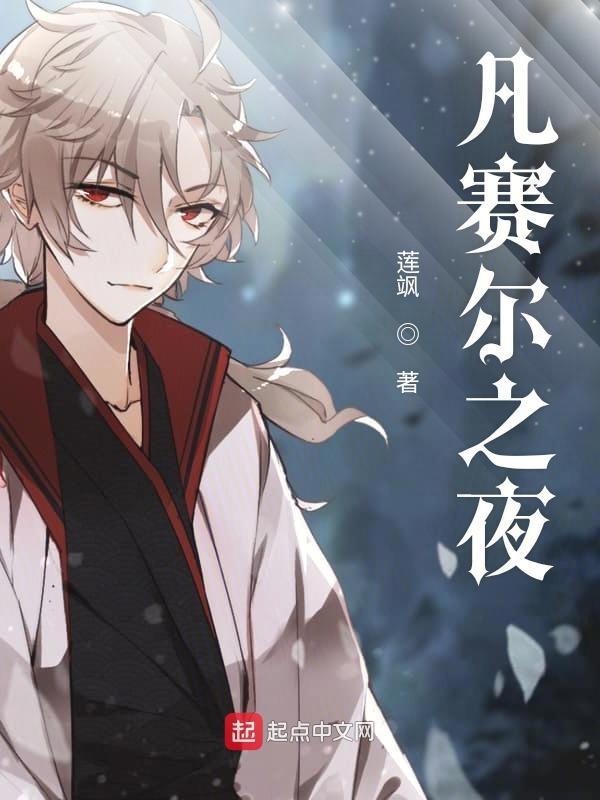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下班别跟钟医生回家格格党 > 第25节(第3页)
第25节(第3页)
时桉抱着大衣,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可衣领还没挂到肩膀,就先被抓住了手腕。
钟严没回头,背对着他说:“怎么还不睡?”
时桉原地转了转,被握的区域有滚烫的温度,像水在上面烧开,“你抓这么紧,我怎么睡。”
松开的手腕被瞬间吹凉,像涂了医用酒精,又打了针利多卡因。
时桉把手腕收进袖口,背到身后,“我去睡了,晚安。”
“不陪我聊聊吗?”
日喀则的深夜,冰冷刺骨的风,时桉想不到留下的理由,却坐到了钟严身边。
请他留下的人并未开口,五分钟后,时桉找来了话题。
“刚才你怎么知道是我?”
“只有你敢半夜不睡觉,给我披衣服。”
时桉:“活该,谁让你那么凶,人人都怕你。”
钟严转头,眼睛像能吸走彼此间的空气,“你呢,怕我吗?”
时桉回避目光,“怕死了。”
“怕我还敢骂我活该?”
“实事求是,不是骂你。”
钟严笑得很轻,“你都什么时候怕我?”
时桉欲言又止,五官堆叠又抚平,“你让我看孩子,我却不敢反驳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为了你好。”
“我不需要。”
“时桉,你怕死吗?”
他早猜到了,钟严一定会转移话题。
“无聊。”时桉说。
“但我怕。”钟严说:”比任何人都怕。”
时桉敷衍,“哦。”
“你知道什么人才会怕死吗?”
“像你这样的人。”
钟严:“是真经历过死亡的人。”
感觉到他不像开玩笑,时桉重新正视问题,“怎么经历的?”
“大学的时候,去地震区救灾,发生了二次地震。我腰部受伤,被埋在废墟九十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光源、没有水源,只有我自己。”
那是钟严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他感受到了疼痛、无助和恐惧。他没有一次那么怕死,又那么迫切地想活着。
想看到光,想被人挖开废墟,想用尽全力活下去。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