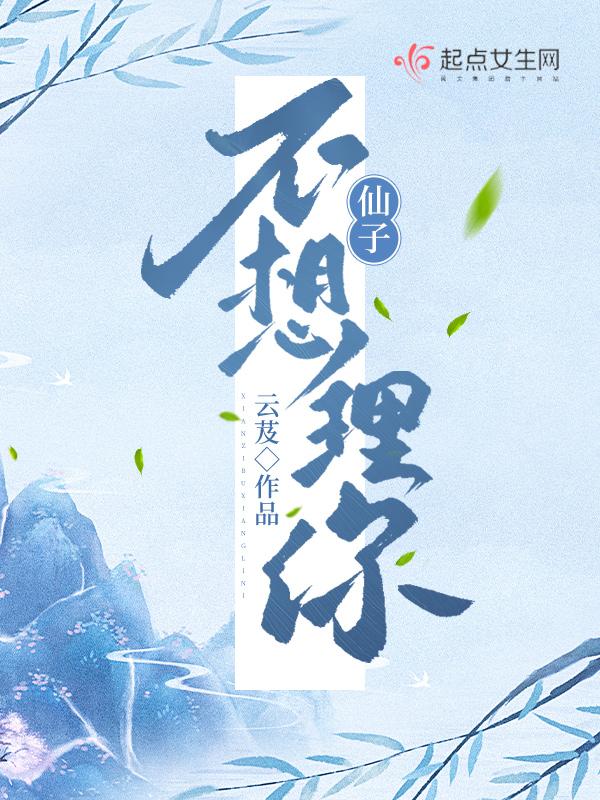格党党>讲不出再见中文谐音歌词 > 第83章(第2页)
第83章(第2页)
“晒起来了,回家。”周景池说。
“我可以解释的。”赵观棋稀里糊涂说出一句话,接着又说:“打架,我可以解释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有车驶过来,周景池埋头将赵观棋往内侧拉。对他说:“我只是想说打架不安全,你本来就受过伤,只怕雪上加霜。”
赵观棋没说话,不知道在盘算什么完美证词。周景池看着那副犹犹豫豫的模样,突然觉得对方被自己传染了扭扭捏捏的烂毛病。
“按你自己的话来说。”周景池去看他的脸,哄他:“你这脸很金贵的,留疤不好看了不是?”
踌躇一瞬,他换了说法:“就不乖了。”
“乖有什么用,你还不是——”赵观棋改口,“你还不是要走一个月。”
他无视好友韩冀的存在,嘟囔抱怨:“我一个人要无聊死了。”
“很快的。”周景池扯着他走在成片房檐的阴影下,“等你下次剪头发,我就回来了。”
在了解到赵观棋童年时光之前,周景池对他粘人的特质是无法理解的。一个有钱的富二代,怎么会有这种几近分离焦虑的毛病。但经韩冀的点拨,加湳風上那场高烧,周景池渐渐明白过来。
人生起病来是脆弱的、纯粹的,往往和孩童一样会向外去求。赵观棋高烧到说起胡话来,却一半都是在喊哥。
开着小夜灯的房间泛着没有温度的暖光,水银温度计被握得发烫。周景池忙到手足无措的时候,窗外又偷摸飘起夜雨来,滴滴答答地砸在彩钢雨棚上。
一点一点,一阵一阵,一股一股,陪赵观棋翻来覆去地闹着。
“哥,你手好冰好舒服。”
“特别好,月亮特别低。”
“这个吃不了,这个过、过敏。”
“我不想爬,我疼。”
“哥,你别哭。”
周景池听得费力,听得糊涂,听得眉头紧锁。发凉的手任由赵观棋抓着贴在脸上降温。安宁一会儿,又激动起来:“我也要、我——”
将耳朵贴得更近,他问他:“要什么?”
烧得通红的赵观棋喃喃道:“我、我也要许愿。”
“不要。”他重复,“不要走。”
燥热的凉夜,周景池悬起一颗喧嚣过虫鸣的心。
整夜静谧,烧渐褪去,注视良久,周景池没再说话,坐在床尾直到天明。
他错了,赵观棋原来是个很能藏事的人。
思绪回到喧闹的天光大明街道,周景池掂了掂手里的口袋,说:“坚持坚持,我回来给你做碗儿糕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