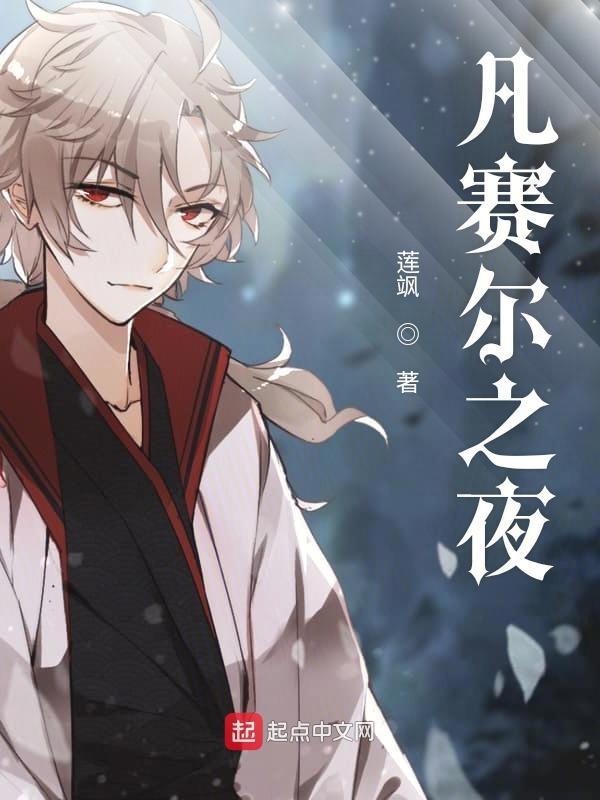格格党>恰如天上月笔趣阁 > 第92章(第1页)
第92章(第1页)
谢候终于发现她哪里不一样了,原是胳膊肘不知什么时候已朝外拐去了。
“既是一家人,又分什么你我!”谢候笑着拉起阿姐的胳膊,涎皮赖脸地晃,“一个好汉三个帮,姐夫再英雄过人,也要有臂膀可用,我也并非全无是处,自不会给他拖后腿,我是他的小舅,又不是外人,总不会……”
“不必再说!”
韶音甩开他,起身便往内室走,“能说动他是你的本事,但我决计不会帮你。”
“阿姐!”
谢候追了两步,见韶音头也不回地进了卧房,不由垂头丧气。门口踯躅半晌,还是叹口气道:“阿姐,有件事我还没告诉姐夫。”
王微之执意过来,他阻止不成,又不想被李勖误会,索性便提早一日出发,将王微之的船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九郎的船,应该明日就会抵达京口了。”
侍从仆婢众多之家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女郎和郎君的低声争吵传到薄薄的菱花窗扇外,门口打扇的婢子知晓了,满院子的下人就都知晓了。
谢候气匆匆地拔步而出,脚步跺得嗵响,上官风端着一碗药从灶房过来,游廊里躲闪不及,被他撞翻在栏杆上,人向后倒栽在花圃里,药碗落到青石地板上砸碎成了几片,黑乎乎的药汁撒了谢候一身。
“郎君恕罪!”
上官风赶紧爬起来,重新跪好在泥土里,上身匍匐着,额头触到了一丛蓬乱生刺的凤尾兰,不知痛一般一动不动地忍着。
谢候吃了一惊,只看着下方人纤弱的肩,心头便忽然浮现出一双紧蹙的远山眉和中间那颗醒目的红痣。
那痣色若胭脂,何忍见其零落泥土?
“起来吧!”他道,人已经迈过栏杆,一脚踩在花圃里,一手将噤若寒蝉的女子拉了起来。
“我们家不像旁人家,不用动不动就跪。再说,是我撞的你,你又没错,有何罪可恕?”谢候说着向眼前女子一揖,“方才急着赶路,不慎冲撞了娘子,还请恕罪。”
众婢子俱都朝着这边看过来,她们早知谢候的性情,忍不住吃吃发笑,上官风脸颊发热,一时不知所措。
晚风拂过谢候的衣襟,他衣衫鼓荡,腰向前折着,面若冠玉,发根黑韧整洁。
一身苦药味。
“郎君的衣服……”
上官风终于想起来这个,谢候已浑不在意地直起身,脸上现出明朗的笑意,像是自嘲:“拢共才见过你四次,两次都赶上我倒楣!”
“我……”
上官风不知该说些什么,谢候已迈开了步子,当先走在前面,引着她一道往西厢房而去。
他不故作深沉时便是这世上最轻盈光亮的所在,能令人郁气尽消,心事一轻。“你阿弟如何了?这趟回去给你们捎了些小物,还不及得给你,正好一道过去探望他。”
小物,他还给他们姐弟带了礼物?
上官风忍不住偷看了他一眼,少年郎君不复刚从阿姐屋里出来那副懊丧模样,像是已将一切的烦心事都抛在了脑后。
“这如何使得?我们不过是……”
“都有!”谢候又抢她的话头,在她启门时先一步推动了门扉,偏头看着她,眉眼都笑,眸光澄澈亮如星子,“阿筠阿雀她们都有,你们俩自然也不能落下!”
都有。
那便好。
上官风垂了眸,眉心痣黯淡在梁椽的影里,“如此,多谢郎君。”
……
夜幕四合时,前院再次响起了橐橐的脚步声,来人身高腿长,步伐很宽,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韶音心里那根弦泠地一颤,是他回来了。
夜风自耳畔呼啸而过,前方是浓重的黑夜,韶音迷迷糊糊地被李勖抱出了门,又迷迷糊糊地上了马,直到此刻方才想起向身后张望。
京口军镇的万家灯火已模糊成一片黯淡的光晕,被他们二人尽数抛在脑后了。
借着长江上一点微光,黑魆魆的山峦在人前显形,巍峨雄壮,天柱昂然,占尽东南形胜,是为北固。
李勖手中的缰绳一松,大宛马便放慢了四蹄,溜溜达达地上了半山腰。明月别枝,甘露庵山门在望,一丛鸟鹊惊飞,扑簌簌的扇翅声自头顶划过,一片槐叶落到韶音头上。
李勖抱她下马,伸手替她摘掉落叶,笨手笨脚间不慎碰歪了她髻上的蝉头玉簪。韶音边整理发髻边歪头瞪他,他笑着将马牵到凤凰池畔,试剑石上栓好缰绳,走回到她身前时忽然弯下腰,韶音的唇上便落了一个又烫又轻的吻。
晚风也织成了轻柔的纱,凉丝丝地拂过发烫的两颊,韶音被他牵着一步步往山上走。深更半夜的山林黑得不见五指,只有偶然从树梢间漏下的几缕月光为行人照明。李勖却走得稳健,他自幼便在这山里砍柴伐荻,就算是闭着眼也能找到路。
过了四面贯通的清晖亭便到了甘露庵外,山门正上方刻着四个红漆大字,夜色中隐约看出前两个是“南徐”。
李勖告诉韶音,那四个字是“南徐净域”。
甘露庵始建于东吴初年,据说是吴国国主孙权为一心向佛的母亲吴国太所建。当年孙权为夺荆州,采周瑜之计,以嫁妹为名将刘备骗到东吴,刘皇叔便是在此庵之中为岳母吴国太相中,因此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当年吴国的刀斧手便是埋伏在韶音和李勖此刻所在的北侧长廊之中,预备在这里砍了刘皇叔的项上人头。
……
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自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再到如今偏安江左的大晋,屈指二百余年矣!汉家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未知孙刘二人得知今日之天下尽归司马氏所有、又在司马氏手里沦落得只剩下半壁残山剩水时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