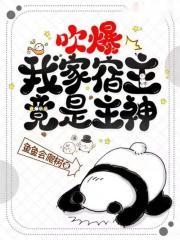格格党>狼王的小狐狸 > 第91章(第1页)
第91章(第1页)
那夜她瞧见茹子昂袖口有些红泥,却也没有多想,以为不过是一些果浆,按照夫妻二人多年的知根知底,又怎么会想到茹子昂会沾上赌场的画押印泥。
“我看门外那些飞禽走狗手里拿的欠条,上面印子清晰,怕是真的。定是在酒里下了药,取了你的手印。”贯丘月兰说,“我看你这个县令,如今也是当到头了。现在家中值钱的东西也搬空了,如今唯有我修书一封,请我大伯出面了。”
“月兰,我”男人佝偻了腰,一句话说不出来。
贯丘家一向看他不顺眼。
贯丘家族看不起寒门出身的穷小子,贯丘月兰本是要嫁给征宁郡一个有头有脸的商会少爷。
自从贯丘月兰暗中资助他读书考试的事情被贯丘家的人知道之后,更是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和矛盾,甚至岳父不顾岳母的反对硬是将独女冷落在外,几十年来不曾联系。
迷雾之城51
其实血脉相连又怎会狠下心彻底断绝关系,贯丘月兰的母亲一直有和女儿暗中通信,只是不敢叫他爹那尊冷硬心肠的大佛知晓。
前不久贯丘月兰才得知大伯又升官了,北幽城的纸醉金迷里,贯丘家自是有了一席之地,太子跟前他们也说得上两句话了。
贯丘月兰的大伯很小就进了北幽都城,得了贵人的青睐,平生都是在宫城里混的。
贯丘月兰起身,步伐小幅度的有些虚浮,茹子昂低着头不敢看夫人,自然是错过了贯丘月兰身侧两只死死握紧的拳头。
她走到书桌前,取下四方玄木笔架上仅剩的一支笔,笔头已经分叉不成样子,想也是极难用的。
贯丘月兰清了清嗓子,茹子昂只能认命地走到一旁替她磨墨。
墨条断成好几截被小心翼翼包在一张浅色素娟里,本是朴素无纹的方正砚台,此时也是豁口裂纹好几处。
这些读书人的东西在强盗看来一文不值,干脆一股脑全部砸烂,也不肯费功夫提那点没用的东西回去。
贯丘月兰虽有时真骂茹子昂是酸儒书生,死板固执得很。但这会儿看到那腰板笔直的书生此时正弯着腰默不作声为她磨墨,没再反对她写信给大伯,她的心又稍稍软了下来。
大门外的叫骂声响彻半边天,屋内的人拿起墨迹未干的信纸朝着上面吹气。
贯丘月兰说:“给我拿个信封。”
茹子昂闻言,低头在杂乱的书架上寻找起来。
“夫人”他挑了一个脏污尚可的信封,双手递到贯丘月兰面前。
贯丘月兰看了一眼,眼角有了些笑意,她的夫君其实也不是全是固执死板,明明旁边还有更干净的信封放着没捡,却选了一个能看出来有些脏污却并不寒碜的。
虽然这声“夫人”颇有一些不确定的劝阻意味在其中,但总算是有些开窍了。
贯丘月兰说:“大伯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你就是放不下你那点不肯求人的自傲,照我来讲,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铅漆封好了,贯丘月兰张嘴还想讲些什么,不远处突然一声巨响。
嘭!
院外的大门倒下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贯丘月兰惊诧道:“怎么回事?”
茹子昂立马正色起来,安慰道:“夫人别急,我先去看看怎么回事。”他一路皱起眉头思虑着接下来的对策。
这些痞子赖子闯进他家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只不过从前都是翻墙或者钻狗洞进来。自从他把唯一的狗洞堵了个严实,还在院子里放了两条恶狗之后,就没人敢再偷偷摸摸来了。
他也想过让府兵进家里来守着,但每个都是满嘴借口故事,都不情愿。茹子昂也没有强人所难,心里跟明镜一般清楚,到底是没人愿意帮他的。
茹子昂很快就回来了,回来时步履匆忙:“阿闫这会儿应当还在学堂,我们不妨先暂避。”
贯丘月兰稀奇地看着茹子昂,从前无论遇到何事,“暂避”这种字眼是绝对不会出现在茹子昂的口中。
茹子昂走了两步见贯丘月兰没有跟上,转头说道:“夫人,还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门外不远处纷杂的脚步声愈来愈近,茹子昂拉起夫人的手就往窗口处疾驰而去。
一大群牛鬼蛇神冲进了茹府,穿过了茹承闫和贺於菟的身体,气势冲冲就往主屋去。就像暗中有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府内的一举一动。
“夫人,这边!”
两人穿过空荡荡的主屋,掀开后窗跳了出去。
贯丘月兰巾帼不让须眉,与寻常女子的忸怩完全不同,只见她卷起两只袖口,提着裙摆跑得比茹子昂还快。
两人贴着墙角,走一段跑一段,混进大街上拥挤的人群中,不想惹人耳目。
两人熟头熟路地到了城东。
茹承闫一路紧追不舍,不肯让爹娘离开自已的视线,前脚跟着后脚到了那块简朴明亮的木牌下方。
长定书院。
茹承闫眼前闪过些许黑白画面,书院门口一只灰扑扑的棉鞋闯进眼帘,老头带着笑的沙哑嗓音比身影更先登场。
茹承闫倏地就红了眼眶。
孔夫子那灰白参半的长须就快比得上他小臂长,佝偻的背部像个小山丘,拱起来好大一块,像是一座山始终压在孔夫子身上。
孔夫子姓孔,学堂里的顽皮孩童都笑他死板迟钝严厉,经常捉弄腿脚不便的夫子,全然没有一点尊敬。孔夫子也经常自嘲,笑自已是大儒孔仲尼的皇亲国戚,虚有其表,败絮其中。
甚至做不到金玉其外。
茹承闫是学堂里唯一一个交束脩的学生,孔夫子也待他特别严厉。